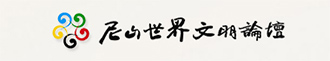对历史剧的界定及其在元杂剧中的鉴别和统计
2020-07-22 09:46:33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赵珂
摘要:历史剧取材于历史仅仅意味着取材于史书而已,并不一定是取材于以往曾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史有其人是不够的,还需史载其事;不论事之真伪如何,关键在于其人其事是否已被传统史学纳入自己的范畴,即看其是否进入了历史系统。如果不是,即便其事属实,也不能当作历史剧。元代的历史剧创作十分兴盛,数量之多占当时元杂剧的三分之一。
关键词:历史剧;历史题材;元杂剧
(一)
什么是历史剧?看起来这似乎不成问题。简单地说,以历史为题材而创作的戏剧都可称之为历史剧。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述解释不仅无法确定一部剧作究竟是否是历史剧,甚至还会引起一场更大的麻烦,即历史是什么?
中国古文字“史”、“吏”、“事”本为一字,它某种程度地展示了历史与官吏和实事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所谓中正是指记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本是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要求,但今天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两点也很值得怀疑。尽管古人修史有“不虚美、不隐恶”(班固语)的实录传统,然而与其说这个传统是一种现实存在,不如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修史者的史官身份必然使其所记的客观性受到削弱。当鲁迅先生赞美《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时,显然也强调了它的主观性——虽然司马迁的观点不一定是官方的。而孔夫子所倡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更是主观对历史的有意识的渗透。即便忽略这一点不论,我们仍然无法“完全”得到历史事实的真相。“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按其定义,所有逝去的就不复存在。准确地说,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所作的‘表述’……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1](P41)而任何一种表述,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具有的想象性和创造性。经过当代各种批评理论探微烛幽的分析,我们没有理由拒不承认这一点。令人惊讶的是,古人仿佛早就模糊地体验到了“史”字里所含带的虚夸、文饰成分。《论语·雍也》云“文胜质则史”,《韩非子·难言》则云“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又,《仪礼·聘礼》:“辞多则史。”郑玄注:“亦言史官多文也。”这对于我们有关历史真实性的概念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事实确是如此。《史记·项羽本记》云大舜、项羽重瞳,据文献载,王莽、李煜亦重瞳。这一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为极其罕见的人体异常现象,竟如此频繁地在中国历代失败的帝王身上出现,或者隐喻了他们的有珠无目?(按,《史记·五帝本纪》称大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大概是被逐而客死蛮荒的曲笔。 他那两个妃子异乎寻常的痛哭暗示了这一结局的悲剧性。)《三国志·先主传》记刘备“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显然不可能是“实录”,这一描写与作者那个时代开始出现的佛教石窟造型艺术正相吻合,不过借此表述模式以展现出刘备的宽厚而已。人类最初尝试表现自己的历史和对历史的看法是神话。我们曾经留心于“黄帝四面”“夔一足”等神话的历史化,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历史的神话化并不只出现在帝王身上。神话——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与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着古人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有时对真实事件的选择以及对其意义的认识竟然也要服从一种神话的模式。人们甚至认为它预定了世上的一切行为。因而,神话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历史甚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左传·成公十年》写晋景公因屠杀赵氏而梦大厉,《南史·江淹传》记其夜梦郭璞索还五色笔而才尽,此皆不宜简单地斥之为无稽之谈。前者是大家熟悉的厉鬼复仇的初型,后者其实与《谢氏家录》所载谢灵运梦见谢惠连遂成“池塘生春草”佳句属同一体系,即杜诗“下笔如有神”一语的情节化,演变到后来就有了洪迅涛《神笔马良》的故事。至于《新唐书·贺知章传》云:“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这简直就是文言小说《南柯太守传》的缩写(时贺氏为京官,此“帝居”当指天帝之所)。我无意在此全面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更无意泯灭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仅就真实性而言,比起文学作品来史籍的可信程度肯定要高得多。我想说的是,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知经常被转化为历史本身,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而当它一旦进入了表述历史的体系之后,便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记载与阐释历史活动中非常活跃、非常富于生命力、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世人的认知是受客观限制的,而人类的认知活动却在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是无限的,所以,当时“真实”的历史经过一个阶段后,却可能变得荒诞不经了。
我们过去对历史剧的限定恰恰在这一环节上出了纰漏。
六十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历史剧的热烈争论,以下述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其一,吴晗《谈历史剧》一文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认为历史剧要不仅要史有其人,还需实有其事,并强调历史剧要“反映历史实际的真实”。[2]这一复制历史的观点今天看来只是能是个美妙的理想。当你尚无法搞清历史真相的时侯,提倡在戏剧里单纯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其二,王子野在《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中说:历史剧“同历史的‘联系’不过是个取材问题,历史剧这个词更准确一点应当称作历史题材的戏剧。”[3]后者的表述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确,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剧作家,其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严格讲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分离开。但王文在具体论述时竟将传统京剧《秦香莲》也划入历史剧,又嫌太宽。到了八十年代,有关历史剧的研讨又趋繁荣,但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两种意见不过是狭义(历史剧)和广义(历史题材戏剧)之别,前者相对于神话题材、传说题材、民间故事等题材而言,后者则是相对于现代题材而言的。本文作为学术问题而提及的历史剧当然应是指前者,其实笔者认为,理论界完全没必要将历史剧生分做狭义和广义两种,它表面上看是消弥了矛盾,实质却是在回避或掩盖矛盾,而那种认为凡是古装戏都是历史剧的观点只会引发学术上更大的混乱[4](P71)。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一个公认而明确的关于历史剧的定义。大家基本默认的标准是,即便是所谓取材于历史,同样不仅要史有其人,也还须实有其事。这一换汤不换药的判别标准对于排除诸如“水浒戏”、“包公戏”及“杨家将戏”等到也确实有效,然而对另外一些作品如“三国戏”等,人之有无好定,事之虚实难度。而像《周公摄政》、《霍光鬼谏》等杂剧中的一些主要情节(周公见疑则稼禾尽偃、疑释则稼禾尽起及霍光托梦诸事)虽于史有征,却难以为真。如果我们因其非真而将类似的作品排除在历史剧之外,显然不合情理,因为它确实是取材于《尚书·周书》和《汉书》本传,是“有历史根据”而又“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将其作为历史剧,我们就必须修改有关历史题材必得实有其事的观念。其实,司马光早就说过一句非常自信而又很实在的话:“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要在高鉴择之。”(《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今天的人走得更远,叙事学界就有句惊世骇俗而又意味深长的至理名言:“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对于我们这样缺乏“高鉴”的普通人来说,既然正史未必真,野史未必假,不妨干脆抛弃辨别真伪的过程,寻找一种更为简单宜行的判别方法。
(二)
西方的历史(historia)概念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文中,“历史”的本义是询问和调查,引伸为询问、调查的结果,就是指史书。这和后来美国的路易·芒特罗斯的观点到颇接近,即“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构建”[5](P268)。我国文献最早出现历史一词是在南朝晋宋之际。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主传》时引《吴书》称其:“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也是指史籍。今天,人们已认识到“历史”所包涵的双重内含。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6](P13)既然如此,我们对有关历史剧的概念也不妨明确如下:所谓取材于历史,并不一定是取材于以往曾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它仅仅意味着取材于史书而已。作这样的规定看起来好象有点画蛇添足,但却使我们的观念和实际情况相吻合,具体操作也更方便。
《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范式(字巨卿)游太学,与张劭(字元伯)为友。后张劭卒,两人之间遂发生了一系列异常的感应:
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式恍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即到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
今天看来,这种神奇的友谊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对某些偶然因素的误解。但在当时,它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是经常出现的。例证之一即南朝乐府民歌中那首著名的《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乐府诗集·清商曲》引《古今乐录》记载了刘宋少帝时的这一感人的故事:
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
上述两个故事时代接近,情节也类似。生者与死者均相距遥远,死者的棺柩皆有所待而不肯前行,甚至在两人之间的感情都得到了母亲的理解这一点上也是不约而同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爱情版。而两个故事又都各自衍生出自己的戏剧作品,前者有元代宫天挺所作的《死生交范张鸡黍》,后者实即始见于宋元南戏至今犹盛演不衰的“梁祝”戏的原型。假如着眼于事件之真实与否,则此二剧以其情节之失真而均不得列入历史剧的范畴。然而,但凡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将两剧一视同仁。毫无疑问,“梁祝”不是历史剧;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范张鸡黍》肯定属于历史剧。也就是说,人们在衡量一部戏是否为历史剧的时侯,实际就是看是否史载其文。因此,本文上述关于历史剧判别标准的议论好像有点堂·吉诃德向大风车挑战的味道。那位认真而古怪的骑士是在和自己的想象力作战,本文则是和我们头脑中史载其文就等于实有其事的观念定势交锋。这个大家已习而不察的观念可以说是历史剧研究中的一个误区,理应得到澄清。
本文强调历史剧取材于史籍而非取材于实事,但所谓史籍也并不单纯。依传统的图书分类,史部极其庞杂,如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载记、传记,甚至政事、时令、地理等都是。这使无疑会增加我们判别历史剧的难度。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搬演东晋温峤骗娶刘氏之事,其事本见于《世说新语·假谲》“温公丧妇”条。虽然《隋书·经籍志》将小说、稗史、笔记等都划归在史部里算作史书,但梁·刘孝标于《世说》注中已力辩其事之非:“按《温氏谱》:‘峤初娶高平李恒女,中娶琅琊王诩女,后娶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刘氏,便为虚谬。”因此,我们应把《玉镜台》排除在历史剧之外。这与本文前面所说并不矛盾。因为其一,《世说》等作品至迟到了《新唐书·艺文志》里已改换门庭,分属子部,不在史书范畴之内;其二,从孝标注对后代的巨大影响而非事之真假上来看,其事显然也已被传统史学所摒弃。(近代以来,史学家有大量雄辩可信的疑古、辨古的论证,但这已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本文对历史剧的鉴定取舍当然不受其影响。)相反,马致远《汉宫秋》的故事本出《西京杂记》,亦小说家言,然此事为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采,已被纳入传统的史学体系,其为历史剧理直气壮。至如费唐臣的《风雪贬黄州》和无名氏《醉写赤壁赋》二剧题材相近,皆写苏轼与王安石不合,被贬黄州,屡遭坎坷困境,终至否极泰来。但由剧本的题目上即可大致认定后者不是历史剧。所谓“醉写赤壁赋”尽管确有其事,有原文可证,然而这篇脍炙人口的名赋,更多的属于文学传统而相对游离于史学体系之外。细读该剧之苏轼醉写《满庭芳》词戏王安石妻以至被贬、邵尧夫预知未来等情节,足以印证其取材于民间传说而非史书。同理,郑光祖的《醉思乡王粲登楼》全从《登楼赋》敷衍而来,也算不得历史剧。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历史剧了。作为一部历史剧,仅仅史有其人是不够的,还需有其事;事有真伪,此尚不足为据,要看其是否出于史籍;史有正史、稗史等,此亦不足为据,关键在于其人其事是否已被传统史学纳入自己的范畴,即看其是否进入了历史系统。如果不是,即便其事属实,也不能当作历史剧。比如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一剧虽有《樊川文集·张好好诗并序》、《遣怀》诗及于邺《扬州梦记》为据,由于这些作品均不曾被传统史学纳入自己的范畴,故仍不得进入历史剧的殿堂。反之,关汉卿《邓夫人苦痛哭存孝》虽事涉虚妄,本文仍取为历史剧。按,史载李存孝因反叛被杀,关作却改其为忠而见疑,受谗被害。这类对历史题材做逆向改动的作品在戏剧史上大量存在,甚至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在时隔不久的元人笔下竟演成一出《赵太祖夜斩石守信》。顺时针画个圆和逆时针画个圆其实都没跳出历史的圈圈。假如不是着眼于历史传统和体系而仅仅拘泥于实有其事或史载其文,对此我们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以削足的方法来维护历史剧的纯洁性不如重新给它订做一双鞋子。至于像王实甫《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那样瞒天过海、把发生别人身上的事“嫁接”过来的作品,当然不宜视为历史剧。道理很简单,如果《破窑记》能算作历史剧的话,下一个就该轮到《窦娥冤》了。历史题材的特殊性正在于其人其事与其时其地的统一,假如任意割裂撮合,则与其它题材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这是就主要的故事框架而言的,因此它不妨碍我们把《智勇定齐》划归为历史剧。在郑光祖的这部剧中,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晏婴竟跑到了战国时代,去为一百多年后的齐宣王和钟离春牵线作媒,对此我们只能认为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虚构。
元杂剧历史剧中几乎到处可见有乖史实的情节,以至于人们甚至怀疑元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剧[7](P20)。笔者尽力对历史剧做出以上的界定,只是要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点。从六十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算起,至今已经四十多了。传说黄河三千年才清一次,想要彻底搞清楚什么是历史剧,也许我们还得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三)
根据上述原则,本文以《元曲选》以及《元曲选外编》所收杂剧为统计对象,即以现存剧本内容为依据对元杂剧中的历史剧进行统计。在《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所收之162种杂剧中,剔除羼杂其中的明代作家王子一、杨景贤、贾仲明、杨文奎、李唐宾所撰10种,共152种,历史剧计有46种,几近三分之一的比例,数量相当可观。具体统计结果见附表:
现存元杂剧历史剧一览表
1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汉卿末本三国外 编
2关张双赴西蜀梦 关汉卿末本三国外 编
3尉迟恭单鞭夺槊 关汉卿末本唐 元曲选
4山神庙裴度还带 关汉卿末本唐 外 编
5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关汉卿旦本五代外 编
6状元堂陈母教子 关汉卿旦本宋 外 编
7立成汤伊尹耕莘 郑光祖末本商代外 编
8辅成王周公摄政 郑光祖末本周 外 编
9钟离春智勇定齐 郑光祖旦本东周外 编
10须贾大夫谇范叔 高文秀末本东周元曲选
11保成公迳赴渑池会高文秀末本东周外 编
12 刘玄德独赴襄阳会 高文秀末本三国外 编
13忠义士豫让吞炭 杨 梓末本东周外 编
14承明殿霍光鬼谏 杨 梓末本汉 外 编
15功臣宴敬德不服老杨 梓末本唐 外 编
16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马致远末本汉 元曲选
17 太华山陈抟高卧 马致远末本南宋元曲选
18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宫天挺末本东汉外 编
19生死交范张鸡黍 宫天挺末本东汉元曲选
20汉高皇濯足气英布尚仲贤末本汉 元曲选
21尉迟恭三夺槊尚仲贤末本唐 外 编
22张子房圯桥进履 李文蔚末本汉 外 编
23破苻坚蒋神灵应 李文蔚末本东晋外 编
24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白 朴末本唐 元曲选
25赵氏孤儿大报仇 纪君祥末本东周元曲选
26鲁大夫秋胡戏妻 石君宝旦本东周元曲选
27萧和月下追韩信 金仁杰末本汉 外 编
28晋陶母剪发待宾 秦简夫旦本东晋外 编
29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狄君厚末本东周外 编
30李太白贬夜郎王伯成末本唐 外 编
31薛仁贵荣归故里 张国宾末本唐 元曲选
32说专诸伍员吹箫 李寿卿末本东周元曲选
33楚昭公疏者下船 郑廷玉末本东周元曲选
34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费唐臣末本宋 外 编
35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孔文卿末本南宋外 编
36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罗贯忠末本宋 外 编
37冻苏秦衣锦还乡 佚 名末本东周元曲选
38庞涓夜走马陵道 佚 名末本东周元曲选
39随合赚风魔蒯通 佚 名末本汉 元曲选
40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佚 名末本汉 元曲选
41孟德耀举案齐眉 佚 名旦本东汉元曲选
42锦云堂暗定连环记佚 名末本三国元曲选
43关云长千里独行 佚 名旦本三国外 编
44诸葛亮博望烧屯 佚 名末本三国外 编
45两军师隔江斗智 佚 名旦本三国元曲选
46摩利支飞刀对箭 佚 名末本唐 外 编
必须说明的是,这46部历史剧可能偶有元明之际的作品,至少一些剧本曾经过明人的加工修订。如果我们以《录鬼簿》(正编)所载剧目为统计对象,它能确保为元代作品,但因很多剧本已佚失,只能由题目正名大致推测其是否为历史剧。两者相互补充,正可大略看出元杂剧中历史剧的概况。以流传最广的曹楝亭本为据[8],原书将鲍天佑、王勉之合著之《孝烈女曹娥泣江》分属两人名下,共447种。因字数限制,本文不再列表。统计结果是,在《录鬼簿》所载446本元杂剧中,历史剧达148种之多(关汉卿《鲁元公主三啖赦》郑廷玉《齐景公驷马奔阵》等剧情不明的本文皆不取),恰也占三分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参酌了刘新文的《〈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一书[9],获益甚夥。惜其未能对历史剧做出较明确的界定,故所收稍嫌杂芜,如《崔护谒浆》(尚仲贤)、《春风杜韦娘》(周文质)之类,其题材并未进入传统历史范围,却都一律收入。又因该书着重故事的探源,同题及相同题材的不同剧作仅择其一,很难全面衡量元杂剧中历史剧的实际创作情况,故与本文之统计结果颇有出入。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吴晗.文汇报[N].上海:1960,12,25.
[3]王子野.光明日报[N].北京:1962,5,8.
[4]沈毅.关于历史剧的正名[J].戏曲研究(16)
[5]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6]张广智.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7]商韬.论元代杂剧[M].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8]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9]刘新文.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2002年7月12日
作者简介:李雁(1960— ),男,山东龙口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编辑:赵珂】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