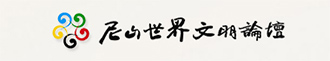公羊三世学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
2022-06-01 10:27:16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宫英英
近世学者研习六经,重视《易》、《书》、《诗》、《礼》,而对《春秋》本身的关注,似嫌不够。特别是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学者,对《春秋》的思想价值,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解读,这是很遗憾的。这从二十世纪经学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上,就可以推知。这其中虽然有学术兴趣的原因,但也无可置疑的,有忽视《春秋》在六经中的重要价值的原因存在。
一、正确认识《春秋》在六经中的独特地位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实际上,六经之中,不独《诗》、《书》、《礼》、《乐》是孔子的教科书,即使《易》、《春秋》,也是孔子教学的蓝本。孔子整理六经,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经过教学活动,使六经得以传承下来,所以,孔子也间接地保存了上古文献。
《汉书·艺文志》曰: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未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孔子整理了《易》、《诗》、《书》、《春秋》,而《礼》、《乐》至春秋而大坏,也依赖孔子的整理。《汉书·艺文志》曰: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又《史记·儒林列传》曰: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於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整理六经,对于《春秋》,则用力最勤,而其效果也最为显著。孔子甚至把自己一生功过的评价都寄托在后世对《春秋》的评价上,而《春秋》之成,的确也起到了预期的目的。如《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司马谈将亡,执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说孔子作《春秋》和为什么作《春秋》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对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春秋》在六经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概括。用壶遂的话说,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作用,就是“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为后世建立一个评价春秋社会人事的坐标。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史记·孔子世家》: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司马迁在这里的论述,也是在阐明孔子为何作《春秋》,以及《春秋》的意义问题。
对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及意义的高度评价,体现了西汉学者共同的认识。西汉初年陆贾著《新语》,其中多次提及《春秋》的意义,如《术事》曰: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
西汉中后期儒学复兴,涌现了大量儒学宗师,大儒刘向更是其中的代表。刘向在《说苑》和《新序》中,对孔子作《春秋》,也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不但认为《春秋》是周德由盛而亡后必然业出现的,体现了继往开来的新德,同时,也赞同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的论断。《说苑·君道》云: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刘向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是非正义感,体现了对天道人事的深刻认识和透彻了解。《说苑·贵德》曰:
仁人之德教也,诚恻隐于中,悃愊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陵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係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恩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赙金于诸侯,《春秋》讥之。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下之为恶尚不可止,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
《说苑·至公》曰: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刘向还认为,《春秋》体现的道,是君子务本的产物。《春秋》对是非的评判,是国之鉴镜。《说苑·建本》曰: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
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
二、正确认识《春秋》今文经学的价值
自汉代以来,有所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分野,虽然从东汉以降,今文经学渐有式微之相,但是,今文经学的真正衰落,却是二十世纪的事情。自康有为之后,近代研究经学的学者本来屈指可数,而因丧失了对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推翻了作为偶像的孔子,也就清除了今文经学生存的土壤,今天的六经研究,不但远离了今文经学,甚至也已经远离了古文经学。
近人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一书中,总结今文学和古文学的不同,提出了十三种分野:
今文学: 1.崇奉孔子;2. 尊孔子为“受命”的“素王”;3. 认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4. 以孔子为“托古改制”;5. 以六经为孔子作;6. 以《春秋公羊传》为主;7. 为经学派;8. 经的传授多可考;9. 西汉都立于学官;10. 盛行于西汉;11. 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12. 今存《仪礼》、《公羊》、《穀梁》、《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和《韩诗外传》;13. 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
古文学:1.崇奉周公;2.尊孔子为先师;3.认孔子为史学家;4.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5.以六经为古代史料;6.以《周礼》为主;7.为史学派;8.经的传授不大可考;9.西汉多行于民间;10.盛行于东汉;11.斥今文经学是秦火残缺之余;12.今存《毛诗》、《周礼》、《左传》;13.斥纬书为妄诬。
西汉学者去孔子不远,他们知道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并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在于推介他的政治主张,他以《春秋》,为天下立德,所以,是春秋时期的精神领袖是“受命”的“素王”,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意图恢复周礼,实现仁政,“托古改制”,不能成功,退而教学,整理六经,为教科书。孔子整理六经,有所选择,如周秦时期晋国太子申生和秦公子扶苏都实践过的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即为不孝的观念,孔子则选取圣人革命的主题和谏父过失的行为规范,并通过教学活动,代代相传。孔子整理《诗经》,立足于“无邪”和兴、观、群、怨之主题,整理《尚书》,则独取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主题,作《易传》,则立足于君子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如此等等,为后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和修身法则。孔子之后,学生遵奉孔子学说,六经之传,虽经秦火,难免有记忆缺失,但师徒授受,仍然弦歌不绝,清晰可考,所以西汉之初,借批判暴秦的时代潮流,得立于学官。虽然今文经学难免有门户之见,但与古文经学徒有文字,而没有系统的师承的口授,微言大义之间有所存,自然是肯定的了。
古文经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因把孔子仅仅看为史学家,没有能洞彻周公与孔子的区别,所以崇奉周公,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所以仅以孔子为先师,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古文经学家只看到了今文经学是秦火残缺之余的历史事实,却没有认识到师徒私相授受的师承优势。因此,尽管《毛诗》、《周礼》、《左传》有其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不能代替今文经学的独特性的。
今文经学的衰亡,和古文经学的兴盛,表面上看,是相信出土文献,还是相信师承的问题,实际上是产生于地方自治政治环境中的思想自由时代的价值观,如何在中央集权时期的专制主义旗帜下寻求生存空间的策略考量。孔子的政治主张,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与专制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所以,孔子从政治家蜕化,演变成了文献家,最多只保留一个传承文化的教师爷的尊严,而失去了政治导师的光环。孔子作为政治家的身份的全面恢复,只有当专制皇权瓦解以后,才可能实现。
所以,孟子在中央集权没有开始的时候,认识到了孔子作《春秋》的价值,以及孔子作《春秋》的深意。《孟子·离娄下》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孔子世家》曰: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至圣,然只有善良而又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孔子作为一个伟大圣人的价值。后世对孔子的尊崇,大部分时候,不过是因其传播六经的功绩。孔子所取之“义”,又有多少时代能够领会呢。
在专制主义即将灭亡的时候,近代民主革命者康有为首先从今文经学,特别是从《春秋公羊学》中找到了革命的思想渊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曰:
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诗》、《书》、《礼》、《乐》并立学官,统于《春秋》,有据乎?据于孟子。孟子述禹、汤、文、武、周公而及孔子,不及其他书,惟尊《春秋》。《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有据乎?据于孟子。孟子发《春秋》之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取之矣。’《左传》详文与事,是史也,于孔子之道无与也。惟《公羊》独详《春秋》之义。孟子述《春秋》之学,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榖梁传》不明《春秋》王义,传孔子之道而不光焉。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
三、孔子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坚守
《孟子·万章下》云: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孔子之所以被孟子认为是圣之时者也,在于他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无所不能的政治洞察力,透彻地了解时代大势和个人际遇的关系,了解天命之不可违抗,知道用行舍藏,能与时进退,人不知而不愠,不为了闻达富贵而进,不为了个人得失而退,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忘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子是个政治家,在他担任行政职务时,无论大小,都有政声。《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 而夹谷之会,更显出孔子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韬略。《春秋·定公十年》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左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巳也。”乃不果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公羊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晋赵鞅帅师围卫。齐人来归运、讙、龟、阴田。齐人曷为来归运、讙、龟、阴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之。
《榖梁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譟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史记·孔子世家》曰: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春秋》三传和《史记》所记,虽然详略不同,而其事迹梗概,大体可以推知。孔子在代行鲁国执政的短暂岁月,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孔子是个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有政治坚守的政治家,这和他同时代及以后的政治家表现出了不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战国时期,如孟轲等倡导王道仁政,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因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但是,“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孔子不答卫灵公的问阵,不是孔子不懂战阵,而是不愿做助纣为虐者。孟子不是不知道当时领导人所好,而是不愿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司马迁对孔子和孟子不愿“有意阿世俗苟合”的认识,正是看到了孔子和孟子作为真正的政治家的本色。
战国时期的成功政治家,常常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功业,而不问政治的良善,趋炎附势,出卖良心。如《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游说秦孝公,曰: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商鞅游说秦孝公,先说五帝天下为公之道,孝公不觉悟;然后说三王德治之道,孝公也无兴趣;商鞅改说春秋五霸之道,孝公以为善;商鞅明白孝公是个功利之徒,所以索性以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道投合孝公,因此得重用。而商鞅自己也知道,以富国强兵之道治国,必然没有办法达到三代的水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又《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先赴秦说连横之策,不被用,而改游说六国以合纵;《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投苏秦,意欲合纵,不被用,而改游说连横之策。苏秦、张仪当面临分裂和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完全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主张,这与商鞅的自甘堕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培养的学生,大多有政治才能,《论语·雍也》载: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在孔子看来,他的学生果敢、通达、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孔子在肯定学生有从政能力的同时,对从政的原则,也是一刻也不放松的。《论语·尧曰》载: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千言万语,为政最重要的是真正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爱护人民,尊重人民。
四、公羊三世与孔子的政治理想
《公羊传》之《隐公元年》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桓公二年》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公十四年》云:“《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提到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解释说:
《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近人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三世》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
董仲舒和何休关于所见、所闻、所传闻,还不算太过离谱,但到了康有为,显然所指,已经不是《春秋》十二世所能概括的了了。春秋时代,实际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康有为以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再把哀、定、昭三世和太平联系起来,把襄、成、宣、文和升平联系起来, 把僖、闵、庄、桓、隐与据乱联系起来,这样的分类显然没有说服力。但是,康有为认为乱世、升平、太平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无疑是有道理的。而且不但有道理,并且符合孔子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所谓“大同”,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天下为家”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征,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假借国家的名义,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力。由于统治者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只好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不公正的统治,并通过强权来推行专制主义人文意识。暴力和强权破坏了自由的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力和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见、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的权利被剥夺了,人民只有服从和牺牲的自由,而没有表示不满的自由,而统治者却逐渐地建立了推行专制主义的自由。孔子心所神往的是人人平等、自由的“大同”,“小康”时代虽能谨礼、著义、考信、著过,刑仁讲让,示民以常,已是不得已,至如孔子之时的鲁国,则违背礼义,“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与“小康”之世相比较,在孔子眼里,无疑又退了一大步。
如果我们把孔子关于大同和小康、乱世的三个时代和公羊三世学说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孔子认为,社会的发展经过了大同到小康,小康到乱世的一个蜕化过程,文教未明的乱世,正是春秋时代;渐有文教的小康时代,是升平世,对应的是夏、商、周三代,即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而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的太平世,则所指应该是五帝时代,以尧、舜禅让为标志。这个三世得蜕化过程,也是商鞅游说秦孝公时等而下之的四个过程的前三个阶段。《道德经》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其论述由道而德而仁而义而礼的蜕化历史,正是由五帝到三王再到霸王再到君主集权时代的文化轨迹,五帝以道治国,三王以德治国,霸王以仁义治国,而到了君主集权时代,则用礼法治国,甚至只用刑罚治国了。
孔子指出了社会蜕化的三个阶段后,认为社会变革,也应该遵循三阶段,进行渐进式的回归。而回归的第一步,就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小康时代,而小康时代有以周代最为进步,所以孔子主张首先恢复周礼,但是礼本身作为家天下的产物,孔子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的。所以,恢复周礼以后,最终还是要向“尽善尽美”的大同方向发展。
恢复周礼,走向大同,最主要的是培养“仁”。孔子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的弟子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爱人”就是以善心对待同类,而其前提就是承认人的平等权利,而对人的平等权利的肯定,也就意味着承认他人的自由。孔子为了贯彻“爱人”的原则,提出了“恕”的行动纲领,学生问他“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作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实现了“恕”,也就是实践了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行为原则的两个方面,都是“能近取譬”的“恕”,其核心是把他人看成是与自己一样有平等权利的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自己不愿意承受的痛苦,绝不能强加于人;自己想实现的愿望,应该允许别人实现。也就是说,要承认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平等权利,不驱使他人,不强迫他人,也就是说,要给他人自由的权力。
孔子在强调“爱人”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给他人自由,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别人宽宏大量。孔子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自由对自己不重要,而是他要教导他的学生去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者只有限制自己的欲望,才能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以模范的行为影响他人,进而创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实现全民的富祉。所以,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就是抑制欲望,“爱人”就是强调统治者与人民的平等,“使民以时”,就是要给人民更大的自由权利。所以,孔子赞扬原始氏族社会的“无为”,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就是不限制人民的自由,让人民自由地生活。
康有为《孟子微》说“不忍人之心,仁也”,又认为:“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一切根,为一切源……太平大同,皆从此出。”他认为,只要从博爱的立场出发,就可以产生平等、自由、民主诸观念,进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与孔子的逻辑线索一致。而谭嗣同《仁学》提出仁——通观念,认为“通之像为平等”,而仁——通——平等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把大同看作是最终理想的观点,我们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找到了佐证。《唐虞之道》以禅让为大仁大义大圣,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自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化民者,自生民则未之有也。”在这里,作者把“仁”、“义”、“圣”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禅让”的理想结合起来,并认为真正的治世的到来必然依赖于建立“禅让”的民主政体,这就使“仁”所具有的平等精神就更加清晰。从而也证明儒家思想决不是维护政治的专制主义体制的,而是把实现大同看作是最后的归宿。
【编辑:宫英英】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
- 让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中华大地持续迸发
- 文化“两创” 时代华彩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尼山讲堂丨杨传召:《中庸》通讲(三)
-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成都进行友好交流,从都江堰治水之道悟治理之道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