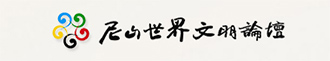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辩
2022-06-01 11:09:21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宫英英
《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后应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而“隐”的释义应该是“私”,孔子的意思是说诗没有表达私志的,乐没有表达私情的,文没有表达私意的,所表达的都应该是合于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同时,应该注意《孔子诗论》第一简意义的完整性,诗、乐、文表达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正是王道教化的功绩,人的动物性的私欲被人的文化属性所取代,正是体现了王道的景象,所以,“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正是紧紧相扣的。而《孔子诗论》的这个思想,也是与传世《诗序》一致的。
一、《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后应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包含二十九支竹简,《孔子诗论》的整理者已故马承源先生把这二十九支竹简分为六部分,其中第一至第四共四支竹简为《诗序》的内容,第五、第六共两支竹简为《讼》的内容,第七共一支竹简为《大夏》的内容,第八、第九共两支竹简为《少夏》的内容,第十至第十七共八支竹简为《邦风》的内容,自第十八至第二十九共十二支竹简为《综论》的内容。其中第一部分《诗序》第一简虽然残破,但是却表达了一段具有相对完整内容的重要观点,马承源先生认为这个第一简可以隶定为以下文字: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
由于《孔子诗论》第一简“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后有一个较粗的墨节,马承源先生认为“这是文章分篇的隔离记号,或者是大段落的隔离记号”,马承源先生指出,由于“《诗论》中还有其他与此相同的二道隔离记号,上下所论都是诗的内容,有可能是大段落的记号”。因此,马承源先生推断,“行此者其有不王乎”这一段话,“据辞文,是论述王道的,这语气和《子羔》篇、《鲁邦大旱》篇内容不相谐和,当然也非《诗序》,由此揣测当另有内容”。如此,按照马承源先生的看法,“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即“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和“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两段话,这两段话涉及到两个大段落,因此,就全文而言,不能说没有关联,在具体文意的把握上,又不能说有什么直接的传承或者隶属关系。
由于马承源先生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从辞意看,应该是《诗论》的首简”。又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几个字“当然也非《诗序》”,所以,按照马承源先生的观点,《诗序》的第一简中心的内容应该是去掉“行此者其有不王乎”这几个字以后,而直接变成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
关于马承源先生的隶定,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前后,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等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以后,这些不同意见先后发表,如裘锡圭先生就曾在《关于〈孔子诗论〉》一文中指出孔子曰中三个“亡”字后的字“可能应释为隐”。关于最后一字,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应该释为“意”字。其释文如下: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另外,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认为《诗论》二十九支竹简应该分为四组,即第十、十四、十二、十三、十五、十一、十六、二十四、二十、二十七、十九、十八为第一组,第八、九、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六为第二组,第七、二、三为第三组,第四、五、一为第四组。李学勤先生认为,“如果以上四组编排可以接受的话,《诗论》全篇始于论国风,其次风与小雅,继之大雅和颂,以通说《诗》旨终结,确是有比较严密组织的著作”。李学勤先生在该文的附录《〈诗论〉分章释文》中,把《孔子诗论》分为十二章,其中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包含了马承源先生《孔子诗论》的内容。李学勤先生的释文如下:
第十一章 《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五……行此者其有不王乎?
第十二章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可以看出,李学勤先生虽然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后面孔子的话是两个段落,这与马承源先生相同,但是,比之马承源先生,李先生无疑更进了一步,他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归宿。同时,李学勤先生认为马承源先生所释“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应该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其认定“隐”字“意”字与裘锡圭先生意见一致。
关于《孔子诗论》第一简,还有一些其他的释文,如廖名春教授《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的释文,虽然仍然与马承源先生一样,把该简仍然放在第一简的位置,但是释文却与马承源先生和李学勤先生有细小差别,其释文如下: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泯志,乐亡泯情,文亡泯言。”
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竹简排列同于马承源先生,关于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则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其释文如下: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
王志平《〈诗论〉笺释》竹简排列同于马承源先生,关于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则释为“吝”字。其释文如下: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
另外,饶宗颐先生也是主张《孔子诗论》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应该解释为“吝”。
何琳仪《沪简〈诗论〉选释》则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应该解释为“邻”,而“邻”又应该读为“陵”,其释文云:
孔子曰:“诗亡陵志,乐亡陵情,文亡陵言。”
可以看出,关于《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中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如何认定,是所有的释文者都很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分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孔子诗论》第一简的字型而言,三个“亡”字后面的字型,释“隐”无疑比释为“离”、“泯”、“陵”可能更准确一些。这也是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问题,上举周凤武的释文,以及陈桐生教授的专著《〈孔子诗论〉研究》,黄怀信教授的专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的释文,在“隐”字的认定上,都和裘锡圭、李学勤先生相同。黄怀信关于该简的次序,也与李学勤先生相同。
另外,关于“言”与“意”的认定上,由于《孔子诗论》第一简底端残破,最后一字已不完整,虽然很多研究者都使用“言”字,但是,裘锡圭先生等人释为“意”,应该更接近古代人的用词习惯。李学勤先生《谈〈诗论〉“诗无隐意”章》除了指出“言”为“意”外,还指出“意”字的写法可以参看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之容庚《金文编》第717页之“意”字,并认为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一句,“实有总括全文之意”。而陈桐生教授虽然用“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的释文,但是对于“言”这个字,却解释为“言意”。实际上就是对释为“言”的积极修补,实际上他也是看出了释“言”不如释为“意”更为妥帖。
二、关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文意的主要见解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普遍可以接受的认识来看,《孔子诗论》第一简的释文,应该是“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理解“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句话的文意,最关键的是如何认识“隐”字的字义,对于“隐”字的字义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对“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句话的理解。
关于其中的“隐”字的字义,裘锡圭先生认为:
第一简的“亡”应读为“无”。诗言志,乐表情,文达意,但诗文之志意不见得一目了然,乐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听出来的。孔子之意当谓,如能细心体察,诗之志,乐之情,文之意都是可知的。所以说:“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隐”有不可知之意。孔子说诗,也就是要明诗之志。
因为《孔子诗论》第二十简有“其隐志必有以喻也”之句,裘锡圭先生认为:“《木瓜》作者通过礼物的投报,将‘藏愿’表达出来,就是使其‘隐志’得‘喻’。这跟‘诗无隐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第一简的“隐”与第二十简的“隐”表达的是同样的含义。如此,《孔子诗论》第一简的意思是说诗没有不知志的,乐没有不知情的,文没有不知意的。
李学勤先生在《谈〈诗论〉“诗无隐意”章》中,详细地说明了《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之言中三个“亡”字后之三字,应该释为“隐”的原因,并认为“隐”就是“隐藏”的“隐”。则《孔子诗论》第一简的意思为诗没有隐藏志的,乐没有隐藏情的,文没有隐藏意的。
陈桐生教授认为“隐”是“隐藏”之意,认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的意思是“诗不要隐藏情志,乐不要隐藏性情,文不要隐藏言意”。
黄怀信教授也是以“隐”为“隐藏”之意,认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的意思是说“诗没有隐藏思想的,乐没有隐藏情感的,文字没有隐藏含义的”。
在上面的介绍中,我们既注意到以“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释文者的观点,也没有废弃以“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释文者的观点,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以“文亡隐言”释文者可能并不准确。同样,我们对于把本应释为“隐”的字,释为“离”“泯”、“吝”、“陵”者,也应该给予关注。
马承源以“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释文,则“离”为“离开”之意,也就是说,《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没有离开志的,乐没有离开情的,文没有离开言的。
廖名春以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泯志,乐亡泯情,文亡泯言”,关于“泯”,廖名春教授认为乃“灭”之意,认为“诗亡泯志”即“诗言志”之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之言应该是说诗无无志,乐无无情,文无无言。
王志平以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以吝为“贪”,吝志为贪志。也就是说,《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无贪婪之志,乐无贪婪之情,文无贪婪之言。
饶宗颐先生《竹书〈诗序〉小笺》虽然也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但是,他认为“吝”应该是“吝惜”的意思。他说:
隐是完全隐藏而不显露,吝是有所吝惜而保留。吝有所惜,故又训为啬。《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亡吝则无所惜,尽情尽意而为之,比“隐”更进一层。“诗亡吝志”者,谓诗在明人之志;“乐亡隐情”者,谓乐在尽人之情;“文亡吝言”者,谓为文言之要尽意,无所吝惜。
何琳仪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陵志,乐亡陵情,文亡陵言”,而“陵”的意思是“凌”,即“越”的意思,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诗歌不可以使心志陵越,音乐不可使感情陵越,文章不可使言辞陵越”。
三、如何正确认识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的文意
我们注意到,上述诸学者,其释文无论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还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以及“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诗亡泯志,乐亡泯情,文亡泯言”,“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诗亡陵志,乐亡陵情,文亡陵言”,多数人都是着眼于诗的言志功能,这说明各位研究者的解释,都是试图抓住了孔子及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问题,所以诸位学者的诠释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虽然如此,我们觉得以上诠释,仍然有重新思考的地方。
比如裘锡圭先生认为,“隐”是不可知的意思,那么,“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的意思就是说诗没有不知志的,乐没有不知情的,文没有不知意的。这个解释完全符合孔子的言志思想,就是说,诗言志,乐言情,文言意。如果说诗言志、乐言情是因为存在者不言志的诗,不言情的乐,难道还存在着不言意的文吗?文本身就是要表达意思的,如果没有意思,那就不是文了,所以,所有的文,都是表达意的。既然所有的文都是表达意的,而某些诗可能不表达志,或者没有表达“无邪”之志,某些乐可能不表达情,或者表达的不是符合《韶》、《武》之情,孔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那么,“诗亡隐志”,说的是诗表达的应该是无邪之志,其意思就应该是“诗不能不知道无邪之志”;“乐亡隐情”,说的是乐应该表达《韶》、《武》之情,而不是表达郑、卫之情,其意思就应该是“乐不能不知道《韶》、《武》之情。应该说,如果把“隐”理解为“不可知”,对于解释“诗亡隐意”、“乐亡隐情”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解释“文亡隐意”,此处孔子要求文所要表明的是何种“意”,如果我们没有对“意”有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界定,其意思一定是欠明确的。
又李学勤先生等人以“隐藏”解释“隐”,则“志”、“情”、“意”或者“言”,就只能存在于普通意义上,所说就是“诗亡隐志”指诗没有隐藏志的,所以所有诗都表现了“志”,“乐亡隐情”指乐没有隐藏情的,所以所有乐都表现了“情”;“文亡隐意”或者“文亡隐言”指的是文没有隐藏意或者言意的,所以所有文都表现了“意”。固然,因为孔子所见诗,都是表达志的,而《诗经》的“志”都是体现“无邪”精神的,然“乐”则有《韶》、《武》与郑、卫之区别,如果不隐藏郑、卫之情,则乐无以道和。《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又说:“《乐》以发和。”又《礼记·乐记》曰: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何如?”
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
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鼗鼓椌楬埙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亷,亷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歡,歡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魏文侯是有德君主,虽然如此,他还是听古乐而欲眠,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子夏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古乐目的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新声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只有声音而已。乐者乐也,乐不同于音,就在于乐有教化的目的。圣人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谓之德音,故称为乐,可以为父子君臣纪纲,为天下大定,郑、卫之音,为溺音。如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君主如果好淫声,必然导致上行下效。圣人以雅乐之鼗鼓椌楬埙箎此六者为德音之音,以钟磬竽瑟和之,以干戚旄狄舞之,以此祭先王,献酬酳酢,官序贵贱,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君子之鼓舞歌诗,绝不是为了音律的铿锵动听,而是为了德治的需要。子夏关于郑声与雅乐的区别,归根结底,就是郑声追求音律的轻柔低靡,引人沉醉于音乐形式之中,追求鼓舞歌诗艺术美的享乐感受,而雅乐所追求,则是音乐背后所暗示的道德力量,是移风易俗的伟大魅力。如果不区分乐所体现的情的性质,只强调不隐藏情,显然,也与孔子的基本乐论精神不相符合。至于文没有隐藏“意”或者“言意”,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表述。因为文都是表现“意”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文无隐意”就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了。但是,有些人文过饰非,所表达又不是真正的“意”,在这个意义上,“文无隐意”又是一句脱离实际现象复杂性的话了。
至于把“隐”释为“离”,即说诗没有离开志的,乐没有离开情的,文没有离开言的,释为“泯”,即说诗无无志,乐无无情,文无无言,两个释义虽然在“隐”字的认定上可能有误,但是所表达的关于诗、乐、文的意思与在“隐藏”的意思上解释“隐”的观点实际上并无不同,其缺憾也同于在“隐藏”的意义上解释“隐”。而饶宗颐先生以“吝”为“吝惜”,认为“吝惜”是有所保留,和“隐藏”有程度的不同,所谓“诗在明人之志”,“乐在尽人之情”,“为文言之要尽意,无所吝惜”,意思实际与解释为“隐藏”并无多大不同。何琳仪以“陵”为“越”所谓“诗歌不可以使心志陵越,音乐不可使感情陵越,文章不可使言辞陵越”,与我们所知的孔子诗论精神,很难建立联系。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解释“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句话,我认为“隐”应该训解为“私”的意思,则这句话的意思就一目了然了。孔子的意思是说,诗没有表达私志的,乐没有表达私情的,文没有表达私意的,所表达的都应该是合于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
按以“隐”训“私”,在传世文献中是很普遍的意思,如《吕氏春秋·圜道》云:“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高诱注曰:“隐,私也,君臣上下无私邪相壅蔽之。”又《文选·颜延年〈赭白马赋〉》有“恩阴周渥”句,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曰:“隐,私也。”《后汉书·钟离意传》云:“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李贤等注云:“隐,犹私也。”而《说文解字·阜部》云“隐,蔽也”,《广雅·释诂一》曰:“隐,翳也。” 蔽、翳的意思,实际和我们所说的“私”的意思紧密联系,都是源于为一己之私所隐蔽,而不能克己。《论语·颜渊》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就是克服私欲,用人的文化属性约束人的类似于动物的私性。
实际上,王志平虽然把“隐”释为“吝”,我们认为是欠妥的,但是,他把“吝”和“贪”联系起来,认为诗无贪婪之志,乐无贪婪之情,文无贪婪之言,这个意思,注意到孔子所论述的是诗、乐、文的一种理想的境界,这个看法,已经很接近我们把“隐”理解为“私”了。因为贪婪实际上就是“私”的一个重要表现。贪婪也必然带来邪恶和壅蔽,对诗、乐、文都是有害的。
按《孔子诗论》第二十简与第十八、十九简,按照马承源先生的释文,应该全是有关《木瓜》的评说文字。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释文者都同意。第十八简有关《木瓜》的释文如下:
因《木瓜》之报,以喻其怨者也。
第十九简有关《木瓜》的释文如下:
《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
《孔子诗论》第二十简有“其隐志必有以喻也”,这句话也是说《木瓜》一诗的。而第二十简所谓“隐志”,也就是第十九简之“藏愿”,这个“藏愿”实际就是“私志”,也就是第十八简所谓“怨”。
四、如何认识《孔子诗论》第一简的逻辑关系
《孔子诗论》第一简云:“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按照马承源、李学勤先生的看法,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在内容上没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根据是“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之间有一墨节,马承源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不属于《孔子诗论》中的《诗序》内容,李学勤先生则把“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放在属于讨论《清庙》内容的第五简后,因为第五简提到了“王德”。
范毓周教授《上海博物馆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和分章》把这个墨节定义为墨钉,与这个墨钉类似的,在《孔子诗论》中,有第五简“颂是也”与“《清庙》王德也”之间的墨钉,第十八简最后一字后的墨钉。大量的是比墨钉细的墨节,几乎每一简都有,而且每一简不止一处。就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墨钉,或者与细的墨节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认为《孔子诗论》的作者用这样的符号来有意识的区别章节,在出土的竹简中,尚缺乏充分的证据来说明。即使这个墨钉真如大家所说的是章的分界,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意思存在很大区别,马承源先生因此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不是《孔子诗论》中《诗序》的内容,而“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意”是《孔子诗论》之《诗序》,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实际上,在孔子及其后学看来,诗是反映世道人心的,只要诗没有表达私志的,乐没有表达私情的,文没有表达私意的,所表达的都是合于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也就是说,王道教化的功绩发挥了作用,人的动物性的私欲被人的文化属性所取代。这是一种体现王道的景象。所以,“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正是紧紧相扣的。《诗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眀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的志的善否,与社会政治的善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诗序》的作者早就揭示的真理。没有私志的无邪的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所以诗也是先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主要工具。治世之音的安而乐,体现政和的特色;乱世之音的怨而怒,体现政乖的壅蔽;亡国之音的哀而思,反映了人民困苦的状态。只有在治世,才能出现没有私志的无邪的诗,无淫情的乐,所以,《孔子诗论》第一简反映的思想,是与传世的《诗序》一脉相承的。那种把传世《诗序》和《孔子诗论》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编辑:宫英英】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
- 让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中华大地持续迸发
- 文化“两创” 时代华彩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尼山讲堂丨杨传召:《中庸》通讲(三)
-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成都进行友好交流,从都江堰治水之道悟治理之道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