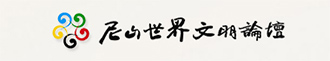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
2022-06-01 11:19:54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宫英英
出土简帛文献强调诗与志的联系,没有志,也就没有诗,这也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核心命题。自《诗经》的作者而后,无不体现出重视诗志的价值判断。而对“志”的重视,就是文学对“善”的追求,“善”是高于“美”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古代文学人文关怀的体现。今天研究古代文学,应该真实地描述古代文人创作的真正目的,把挖掘古代作家对人文关怀的关注,当作我们的重要研究目的。
一、无“志”即无诗
郭店楚简的作者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曰:“诗亡离志,乐无离情,文亡离言。”可以看出,在出土简帛文献中,“志”的问题,是是的根本问题,诗的创作目的,就是体现“志”,无“志”,也就无诗。
事实上,“诗言志”,文学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著作形式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标志,这在传世文献中有大量证据,在出土文献中也是多次被证明了的。战国竹简在说诗时,毫无例外地强调其“志”,并把“志”看作是区别诗与其他著作的标志,“志”与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就是说,没有“志”,也就没有诗存在的价值。所以,刘勰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情”与“志”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情”侧重在主观直观感性的感受,“志”则更多强调已经超越主观直观感性的客观理性的成分。
在中国古代,最早被我们今天纳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是诗歌。古代作家和学者对于诗歌的创作目的,以及诗歌的功能和价值,有许多经典的论述,这些论述所表达的意见,是诗歌之所以产生并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诗歌创作的目的,没有功能和价值,诗歌就不可能产生,我们也就无从谈起研究诗歌这样的文学。
关于诗歌创作的直接目的,《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这里,作者对诗创作目的的概括,只有一个“志”字,而不及其余,对歌、声、律,也只强调其形式特征。这说明诗这样的文学形式的存在,其价值首先在于其精神和内容功能。《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说明诗之“志”是有关人生与人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感触和评价的,诗是体现以人为根本的价值观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创作出来的,是人文精神的直接的体现,所以,《诗序》的作者认为在诗歌中可以看到“治世”、“乱世”、“亡国”诸特征。
《诗序》立足于以《诗经》各诗篇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来解说诗意,其立论在于“美刺”、“兴寄”,即以文学关心人生,关心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是论者都不怀疑的。不过,今天仍然有大量学者怀疑《诗序》的可靠性,所以,我们不妨从《诗经》中明确有原初作者陈述创作动机的诗篇中找直接的论述,如:
1.《魏风·葛屦》曰:“维是偏心,是以为刺。”
2.《陈风·墓门》曰:“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3.《小雅·节南山》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4.《小雅·何人斯》曰:“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5.《小雅·巷伯》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6.《小雅·四月》曰:“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7.《大雅·民劳》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这些诗句,本身是诗的一部分,其代表作者的意志,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知道,《魏风·葛屦》的作者作诗的目的在于批评主宰自己命运的君主的偏心,自己与夫人(所谓“好人”,即美人)的处境迥然不同。《陈风·墓门》的作者有鉴于陈佗的不良(又说刺陈桓公不能去陈佗),作诗以警告。《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作诗,是为了讨伐周幽王重用小人师尹。《小雅·何人斯》为诗人绝交之诗,声讨反复无常的小人。《小雅·巷伯》的作者寺人孟子,作此诗的目的,是为了诅咒周幽王的听信谗言,暴虐无道。《小雅·四月》的作者写诗,是大夫为了发泄对周幽王的不满而发出的哀告。《大雅·民劳》的作者写诗,是为了批评周厉王之追求珠玉美女。
《诗经》的作者创作诗的动机非常清楚,就是要通过诗,体现对集体或者个体生存环境和生存境遇的关怀,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言以蔽之,就是“诗言志”。
非但“志”、“情”对诗如此重要,对其他文学样式,也同样如此。《楚辞·九章》多次言及屈原之创作动机,《惜诵》曰:“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抽思》曰:“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悲回风》曰:“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屈原的这些论述,包含有“情”、“志”两者,言志、抒情,正是屈原创作楚辞的直接动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以其作品,体现存君兴国之志,发愤之情,与《诗经》的传统一脉相承。
屈原之后,宋玉创作大量赋文学,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或讽谏楚王关注平民之苦,或为自己的人格品德辩解,“情”与“志”存在于字里行间。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司马相如之赋,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虽有侈艳的形式,雕琢的语言,但是,作者创作赋的目的,或者说赋的最终归宿,则归于讽谏。至于客观效果如何,则不仅仅是作者的责任了。《汉书·扬雄传》曰:“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扬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逐贫赋》、《太玄赋》诸赋,或表达讽谏之“志”,或表达孤寂落寞之“情”。刘勰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文学需要“丽辞雅义”,但是,“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个“大体”,或者称为“质”、“本”,就是“志”,背离“志”,就是舍本逐末,所以,刘勰批评说:“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因此,赋文学之创作动机,同样也不可背离讽谏之“志”这个根本。
二、古代文学注重对社会及人生发挥积极影响
和诗人的创作动机及目的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诗的内容问题,《论语·为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是诗人创作动机及目的纯正性和合理性的必然体现,是孔子删诗,诗三百篇能列入先王政典,成为体现“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范本的重要原因。《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充《论衡·正说》曰:“《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篇。”孔子删诗,其目的,就是要保存那些体现无邪精神,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功效,教人向善的诗篇。
创作动机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功能。诗的功能,与诗创作的动机联系在一起,作者阐述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动机,着眼于主观愿望,学者论述诗歌的功能,立足于客观效果。也正因此,诗的功能与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古往今来,论文学之功能,最全面、准确、深刻者,无有逾孔子者。孔子之关于文学功能的论述,见于他讨论《诗经》的文字中,现择大家最为熟悉的几条,罗列如下:
1.《论语·泰伯》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2.《论语·子路》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
4.《论语·阳货》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5.《论语·阳货》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在孔子看来,诗的功能体现在个体修身的层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层面。修身必须以读诗为始,不读诗则不能在社会中立足,不可以成人,同时,读诗又必须把个人修身与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所以,要能为政,使于四方。也就是说,诗歌不仅仅是体现个人之哀乐,还要通过对个人哀乐的表现,成为培养人格、实现美好政治理想的工具。即文学必须体现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文学应该关心人,关心人的成长和生活,反映人的喜怒哀乐。
如果我们把《礼记·大学》中关于修齐治平的思想与孔子的诗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读诗,正是孔子倡导的实现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治国平天下应始于修身齐家,修身齐家则应从正心诚意开始,正心诚意又依赖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从读诗开始,无疑正是孔子“兴于诗”的意思所在。
《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艺文志》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的功能可以使王者自考正,当然可以让士大夫知自立,自强,自爱,自重,所以,荀子发挥孔子“兴于诗”的说法,强调学习之“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修身之“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如此,包括《诗经》这样的经典,正是君子格物致知的必然途径。所以,孔子对于诗的要求,就不仅仅是“尽美”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尽善。《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以天下为大同,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孔子在这里虽就乐而言,但诗乐舞在中国古代的同一性,使《韶》、《武》必然包含诗在其中,更何况“乐”本身在孔子的修身体系中,是最终的境界,所谓“成于乐”。
孔子所以强调《韶》的尽善尽美,就在于《韶》体现了大同理想,而《武》却无此精神,所以有美而无能至“尽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到达“尽美”的高度,并不是顶点,还应该再向前走,就是达到“尽善”,“尽善”就是文学作品必须体现出大同的精神追求,文学作品只有在内容上体现出“尽善”的高度才是符合孔子审美理想的终极追求。
追求善,戒除不善,是孔子一向的追求。《论语·述而》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季氏》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对善的追求,对不善的警惕,在这些论述中已一览无余。正像孟子所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积极于善,与人为善,必然归结为追求大同;反大同,必然与人为恶,屈服于私利的驱使。所以,孔子赞扬善,与他赞成大同,正体现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孔门对善的重视,也体现在《易传》之中,《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重要的思想著作,其强调善,也与《论语》无二,《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有》象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益》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系辞下》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而《礼记·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至善的追求,实际就是孔子对文学价值和功能的期望,也是孔子重视文学的最直接的原因。
孔子对善的追求,体现在他的审美理想之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善,对于文学作品来讲,就是强调文学作品内容的至高无上地位。一切文学作品,其最终的归结点,绝不仅仅是文采的愉悦,形式的超凡脱俗,而是对人的关怀,只有善,才是符合人文精神的追求。文学的人文功能,在人格至善的同时,也包含了政治的至善,所以,文学应该批评不良政治。《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讽谏君主,批评乱政,正是“志”的体现,孔子把“至善”寄托在大同理想,就是对政治至善的期待。
正因为孔子认为《韶》体现了他的大同的审美理想,所以,孔子对《韶》的赞扬还有不少,《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卫灵公》云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吴公子札在鲁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象箾》、《南籥》为颂扬文王之乐舞,《大武》为武王之乐舞,《韶濩》为汤之乐舞,《大夏》为夏禹之乐舞,《韶箾》为虞舜之乐舞。季札是孔子理想所寄托之人,其审美判断同样折射了孔子作《春秋》的意志。
三、古代文学评价要体现人文关怀
今日社会是一个强调现实价值的实用主义时代,这个实用主义的时代特征,就是强调一起行为的目的性和合目的性。对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又是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庸置疑,并且在当代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同时,古代文学的存在,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灵魂的呻吟,是古代文学家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社会境遇的真实感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伦理,是非感和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个人人格高大,并坚持而不动摇。而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未来的作家和学者来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古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挖掘古代文学所包含的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由个体人构成的集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利意志带来的社会不公的揭露,对黑暗政治的批判这样的人文精神。研究古代文学,目的既是为了了解历史,同时,也是为了把古代文学家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贯彻到我们今天的文学评价体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古代文学之时,有义务、有责任挖掘古代文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并把这种社会责任和独立人格的内涵介绍给当代学者和读者,以此作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基础。
古代“文学”的概念,实际包含了今天的几乎所有的人文活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充分的人文内涵,这就要求古代文学研究主体,即研究者应该具有人文关怀。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防止所谓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艺术”等给文学加上了特殊定义的观点。有学者公开强调“文学就是文学”,而他所说的文学概念,既与汉语“文学”一词的本意无关,而且也比西方社会所说的文学概念狭窄。某些教科书在确定其研究范围的时候,再次强调“文学”的纯洁性,要写所谓的“纯文学史”。因此,他们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文学“本分”,而此“本分”实际背离文学之“本”,所以,他们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把一首诗或者一部小说的美挖掘出来,让读者能享受诗和小说的音节之响亮、语言之光灿、情节之曲折,而忘记文学欣赏“得意忘言”的主旨。
“纯文学”论者在实践中看不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把文学局限在艺术领域,热衷于讨论文学的形式美感和文学修辞技巧,以此来发挥在中国古代并不占主流地位的严羽、司空图的理论观点。虽然当代研究者对艺术形式的重视是针对过去古代文学研究成为政治斗争附庸的惨痛教训,但是,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并以此为评判文学的主要尺度,那就忘记了古代文学产生及存在的最根本、也是最原始的创作动机和功能,因而放弃文学曾经具有的社会责任,堕落为刘勰批评的“逐末”之徒的行列。毫无疑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必然会有过犹不及的缺憾。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即文学为什么产生,有什么创作动机,我们又如何去明文学的“本分”,又如何去把握“纯文学”的尺度?如果按照纯粹形式美感的标准去把握,文学就应该变成“修辞学”,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不再是包含了思想与情感的实在的活灵活现的体现人类灵魂的载体了。如果这样,文学的价值和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必然变得无足轻重,中国古代文学家的丰富的创作活动,以及他们所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就会逐渐失去其光华,而研究古典文学本身,就成为一件非常无聊的,无益于现实人生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忽视文学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倾向,在古代各个文学发展阶段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当然也受到了各个时代有责任心的学者和作家的批判,如汉赋,如六朝美文,如形式主义诗风等。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不是忽视文学形式之美,而是强调文学形式美感总归是要服务于文学之“志”的,所以,孔子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扬雄眼见赋文学之讽谏没有效果,则曰“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即《诗经》的作者不忘突出其“志”,而汉赋的作者过分注重形式美,而淹没了讽谏之初衷,扬雄有鉴于此,所以得出结论,认为过分注重形式,必然“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刘勰认为内容为形式淹没,或者乌有情志,即无骨干,《文心雕龙·风骨》曰:“脊义肥词,繁杂失统,无骨之征也。”所以,认识文学内容比形式重要,是文学创作所必须牢记的,所以,《文心雕龙·定势》曰:“情固先辞。”刘勰分析了“为情”和“为文”的区别,警告“为文”的危害性,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者的借鉴,《文心雕龙·情采》曰:“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赋颂,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如果把文学之属于语言修辞层面的特点凌驾于文学所体现的情志之上,今天的学者不正在把古典文学变成了“逐文之篇”了吗?显然,这是违背我们今天的学者的研究目的的。
【编辑:宫英英】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
- 让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中华大地持续迸发
- 文化“两创” 时代华彩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尼山讲堂丨杨传召:《中庸》通讲(三)
-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成都进行友好交流,从都江堰治水之道悟治理之道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