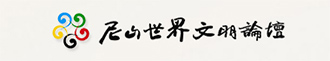孔子与战国文学的繁荣
2022-06-07 17:36:33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宫英英
《史记·六国年表》以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七雄历史的起点,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6年。习惯上,把这一年看作是战国的开始。战国经二百余年的风云变化,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建立秦王朝,而宣告结束。战国文学就是产生在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战国文学,深受孔子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孔子的教学活动培养了大批文学家
在先秦时代,“文学”是一个比现代定义更加宽泛的概念,大致说来,一切文化学术活动,以及从事文化学术的人都可以称为“文学”。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普通人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因此,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也可以称为“文学之士”)以及他们创作的著作(即“文学”),都谈不上繁荣。今人罗根泽研究先秦诸子,有《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探赜索隐,发见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及其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春秋时孔子等所用教学者无私家著作。因此认为“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战国前无私人著述,所具有的,不过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官府“政典”。
战国之世,私人著述大量涌现,诸子九流十家,著作数千百种,据《汉书·艺文志》,今存有《孟子》、《荀子》、《晏子》,《黄帝四经》、《管子》、《文子》、《庄子》、《列子》、《 鶡冠子》、《道德经》,《商君书》、《韩非子》,《墨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尸子》、《尉缭子》、《吕氏春秋》等,阴阳家、名家、农家、小说家著作,皆残缺不全。诸子之外,又有史传和辞赋。史传主要是《左传》、《国语》、《战国策》。辞赋则包括荀子、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作家的作品。
战国文学如此之繁荣,推本溯源,则不能不称赞孔子开设私学的功绩。孔子教学,有教而无类,“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招收学生,不论等级,使普通平民通过学习可以成为文学之士。《荀子·王制》称:“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正是指的这种情况。《荀子·大略》举例说:“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子赣、季路都是孔子的学生。这种私人讲学风气,在孔子弟子那里,仍然得到继承,因此更多的出身庶人皂隶工商之贱人,通过努力学习而忝列士林。《吕氏春秋·尊师》云: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子夏为孔子学生,墨子受教于孔门,禽滑黎为墨子弟子。他们开门论道,聚徒讲学,皆受孔子之赐。
庶人、鄙人只要学习了文学礼义,就可以成为士。士的队伍扩大了,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之士大大增加了,文学也就逐步走向了繁荣。
二、孔子开启了自觉著述的新士风
孔子及其弟子,教学对答,往往以成为“士”、“志士”、“士之仁者”而自勉。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弟子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在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心目中,“士”应具有学识、志向、道德、仁义、忠信、勇敢之品质,同时,又有使于四方的外交家之政治才能。士的志向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对天下具有强烈责任心,同时又注意自身才能智慧的培养。正是这种新士风,造就了战国文学之士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既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也表现为通过著作以拯救现实社会。《史记·孔子世家》 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行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整理经典,使之流传后世。《孟子·滕文公》说孔子做《春秋》的动机时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个意思,《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董仲舒的话说得更清楚。董仲舒指出:“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以深切著明的行事,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孔子意欲通过著述的形式拯救社会,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创作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战国文学之士是普遍认同的,也是身体力行的。
战国诸子自觉地通过其著述,以表明自己的主张。著述,是战国诸子参与现实,体现其现实使命感的一种方式。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游说诸侯不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孟子·滕文公下》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肯定荀子“嫉浊世之政”而著作数万言。又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而“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孟子、荀子、邹衍、邹奭等人自觉的创作意识,及其现实使命感,于此可见一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屈原创作动机云:“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九章·抽思》曰:“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屈原创作楚辞,既是其发愤抒情的方式,也是他借以表现“存君兴国”目的的途径。屈原的行为,充分代表了战国时代文学家自觉地运用创作以实践其现实使命的责任感。屈原自觉地运用文学“显暴君过”。不韬晦,在打击面前,批判恶势力不遗余力,咒骂群臣的奸佞,世俗的丑恶,君主的骄淫多变,甚至对天命,都有所不满。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屈原宁愿自杀。《离骚》 曰:“伏清白以死直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怀沙》曰:“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都表明其不与邪恶势力妥协,誓为一死的士人的决心。
三、孔子的文学观是战国文学思想建立的基础
孔子以“文”教育弟子,其学生子游、子夏以“文学”成名。《论语》一书,收录孔子论述文学问题的观点,其中心是重视文学的强大社会功用。《为政》说诗,曰:“思无邪。”强调诗歌内容之纯洁性;《阳货》则认为诗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之功用,即文学必须有利于社会人生。这些看法,奠定了战国文学观念的主旋律。它是文学肯定论者重视文学,强调文学发挥强大社会作用之论点建立的根据,也是文学否定论者否定文学及其作用的出发点。
战国文学观,基本立场是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从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不同认识,派生出文学肯定论和文学否定论。
儒家是文学肯定论者,他们强调文学对社会所起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因“世衰道微”,作《春秋》,取古史《乘》、《梼杌》、《鲁春秋》等“义”,继《诗》而起,担负起“天子之事”,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所蕴含的是与《诗经》的作者同样具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感。
荀子作为儒家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强调博学与文学的重要性,《荀子·劝学》曰:“学不可以已。”《荀子·大略》曰: “人之于文学也, 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把文学视为人的修养之重要内容,这正是对孔子重视“文”、“文学”主张的继承。
墨家非乐,因而排斥文学之“美”,此与儒家不同。但追求文学之实用,并不背离孔子重视文学功用的观点。《墨子·非命下》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也就是说,文学必须为万民利益服务。为实现文学的目的,墨子提出三表之说,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文学创作之根本在于言必以古圣贤之事为准则;而文学创作之立言,要以百姓的实际体验为依据;文学之用,要贯彻到政治实效之中。不能有本原实用之文学,《墨子·贵义》称之为“荡口”,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常”为尚之义,“荡口”即无根据的言辞。
如果说儒家诸学者表现出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之倾向的话,道家则倾向于否定文学。他们之所以否定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无用。其立论要点如下:
首先,文学并不足以表现真正的思想精华,《庄子·天道》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还举轮扁之言以为喻,轮扁斫轮,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父不能以喻子,而此规律,得之实践的总结,是真正的精华所在,却随着领会了此精髓的人进入坟墓之中,而留传到世间,并被记录下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不过是“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秋水》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也。”言粗而意精,言意之外,又有无形之物,“数之所不能分也”。言论虽可记录有形之语言和具体的情态,然而情态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有内在、外在诸作用共同推动,我们所能观察的,不过是外在的东西而已。我们认识某现象世界而通过言论表达出来,事实上并没有透过现象此表象而深触根本。加之世界无限丰富,又有难以言论、意致者,这样看来,我们用文学等形式表现某种观念,岂不是很徒劳。
道家不但认为文学不能表现真正的“意”,同时还认为文学等“文明”的成果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庄子·胠箧》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也就是说,圣知、六律、文章、五采,是引起争竞、奸诈、巧伪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当然也是引起社会混乱,破坏朴素、纯真、宁静的自然氛围的因素之一。
《庄子》的上述看法,同样也反映在《道德经》和《黄帝四经》等著作中。《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道、名皆具有神秘的自性,是不可以说明,不可以用名来定义的。因此,真正具大智慧的人,是不言的。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道德经》对人类文明的智慧持否定态度,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聘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种把文学之美与内容、人格之善对立起来的态度,与《庄子》是完全一致的。《黄帝四经·称》曰:“实谷不华,至言不饰。”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反对文饰而重实用的观点。《经法》曰:“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即认为虚夸修饰,以为文华之美,是社会混乱的根源。
法家自商鞅至韩非,都是以文学为害虫的文学否定论者,《商君书·农战》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也就是说,文学之士的文学活动,会引导千万个农战之士趋而向风,遂使无人耕战。所以,《农战》又说:“《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守。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鞅显然把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文明与国家的富强繁荣等物质文明对立起来,认为精神文明有害于物质文明。在某些场合,他把精神文明的内容称为蠹害国家肌体的“六虱”,《商君书·靳令》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礼》、《乐》、《诗》、《书》等传统经典,所宣扬的是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因为其好德治,所以非兵而羞战,这与法家的目标显然不一致,这样的精神文明,在法家看来,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污染”,是一种“自由化”的思想倾向,因而可比之虱。
商鞅在大部分时间是否定文学等精神文明的产品的,但这种否定主要是基于缺乏符合法家所需要的主题的文学。如果文学能为法家主张的发扬服务,则另当别论。《商君书·赏刑》云:“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即以歌颂耕战的诗歌民谣代替宣扬礼乐仁义善修等内容的传统文化。所以,法家的文学否定论不是不要文学,而是不要传统道德的文学,通过对旧的文学内容的否定,建立一种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耕战文学。
韩非继承了《商君书》中的文学观,《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以文学害用,而称为国家蠹虫,因此,特别强调“息文学而明法度”,认为“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二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反对文辞之修饰辩慧。
韩非主张一切行为的功用原则,息文学,禁辩丽,是缘于文学辩丽无益于用,而有害于世。《韩非子·问辩》指出:“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解老》曰:“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如果违背了功用的目的,一切言论行为不过是所谓“妄发”而已。恃貌饰而论情质,其情质无美,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取情好质,去貌恶饰,即文章惟以表达情感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的华美。
《吕氏春秋》是杂家著作,它关于文学创造动机的看法符合文学有利社会人生的观点。《达郁》曰:“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国郁”积聚,将危社稷,而语言可以通上德,达民意,表达作者或说话者的欲念,因而文学等言说,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种看法,正是孔子文学观所倡导的。《贵直论》曰:“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雍塞》曰:“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直言决“国郁”,主要是见枉与过。文学如能尽此政治责任,则无疑是可以肯定的。而君主容许文学之士存在,也正是基于此目的。所以《吕氏春秋·贵当》云:“故贤主之时见文艺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务也。”
《吕氏春秋》贵直言,又贵信言,即言与意合,意与事合。《贵信》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贵信与贵直一样,也是出于其功利的目的。信立,则虚言可以鉴,用之世事,无往而不尽其用。
四、孔子整理的六经为战国文学提供了借鉴
儒家推尊六经, 但六经并不是儒家创作的经典, 而是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有详细之说明,曰: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迹,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古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易》此书经庖牺氏、周文王之手而成,《书》、《春秋》是史官记言、记事之载籍,《诗》是采诗官收集,以供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工具。《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皆是根据具体之需要,而由君主或君主任命的官员所作。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对六经予以重新厘定、整理,并传授给弟子,因此六经能广泛流传,成为战国前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总汇,是它以后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参照物。关于这一点,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看得最清楚,《庄子·天下》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又《礼记·经解》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所标榜,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认为,六经的这种特点体现在文学内容及形式方面,是所谓“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并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具体而言,“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所以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即内容的纯正与形式清约简丽。
战国文学之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六经的影响,荀子更倡导征圣宗经之观点。《荀子·儒效》曰: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荀子之言诗言其志,指的是《诗》为圣人人格之表现,此与《尚书·尧典》宽泛地说“诗言志”不同。王先谦《荀子集解》曰:“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也即《毛诗序》之“发乎情,止乎礼义”。“文”指文饰;“光”者,广也;“至”指“盛德之极”。在荀子看来,《书》、《礼》、《乐》、《春秋》其言事、言行、言和、微隐,与《诗》之言志相为表里,构成一个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大系统。文学正是养成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途径之一。《荀子·劝学》曰: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书》之政事,《诗》之情态,《礼》之行为纲纪,《乐》之中和,《春秋》微言而大义,可以教导人超凡入圣,所以是学习的最高典范。
荀子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他对于《易》、《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流传,居功甚伟,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传授,既发现了圣人孔子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五经是圣人智慧所具有情志文采的完善体现,所以学习必须以圣人及圣人创设的经典为根据,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圣人,同时,他又发现了五经各自的特点,如“《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的特点,即“《礼》、《乐》标举法则而无论说分析,《诗》、《书》记载故事而不切近当前,《春秋》文辞简约,意旨微妙,一时难以索解。”所以在学习之时,“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即要通过师徒传授认真地领会五经意旨。
荀子以征圣、宗经、明道的纲领为基石,发表了他对“言”、“名”、“乐”等问题的看法。《荀子·非相》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所谓辩,就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言谈,文以明道,君子好辩说,正命名而辨异同,是基于卫道的目的。道关乎治乱人情,心之与言、说、辞、命,必须合于道,而道则以礼义之顺,合于圣人。背离道,名不合实,虽辩丽,也是应抛弃的。言、名的道理,用于文学创作,便是对文学内容明道目的和文章用词命意切实的一种要求。
论战国文学之源头,不能不提到《论语》,《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最后辑成书籍,当在战国之初,但所记语录,多出自春秋末年孔子之口,因而以《论语》来说明战国时人的思想及写作艺术,肯定有牵强之嫌,但以《论语》所反映的思想为传统思想之结晶,无疑是恰当的。孔子是儒家祖师,其思想也是战国儒家最基本的主张,对孟、荀诸人的影响深远,其论文学,强调学文的重要性,强调文学要具有事父事君、兴观群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相称,并以“一家之言”的辑录形式,成为诸子著作之典范。
《汉书·艺文志》以诸子出于王官,这是缘于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及孔子而后,开私人讲学风气。诸子开坛讲道,收授门徒,正是效法孔子。《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作为对六经思想的集大成思想,为战国儒家奉为圭臬,也成为反对传统学说的诸子建立自己论点的参照系。孔子带领战国士人志向学文,他对文化典藉的重视,对文学的重视,启发战国士人纷纷建立其学说。《论语》在艺术上,作为语录体散文之蓝本,其所记多为生动精辟的格言和警句,通俗而又具形象性,并善于通过人物富于个性的语言、行动来展示人物性格,特别是通过简洁的叙述,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塑造了孔子这个好礼仁义,幽默机智,宽惠慈爱,关心民生的伟大圣人的形象。《论语》虽不在《诸子略》中,但它的出现,开辟了个人著述的先河,其对战国文学,特别是战国诸子散文在思想与艺术手法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五、战国文学是六经的新发展
《庄子·天下》论六经之学,认为“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又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认为六经的内容与诸子百家学术的联系与区别表现为六经的道术为诸子百家所吸取,但百家未能融汇贯通,所以各执一词,不能兼备众善众美之纯正。这个意思,《汉书·艺文志》也曾有陈述,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今人马一浮先生有“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观点,其要点有二,“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战国以前中国文化之集大成之作,是一切学术的必然出发点。但这并不等于六经之学是神圣不庸怀疑的。儒家传六经之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到梁,梁惠王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君主都欲合纵连横,以求攻伐之速胜,而孟子却述唐、虞、三代之德,《汉书·艺文志》述儒家之弊曰:“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远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也。”六艺之学的衰落,不仅是由于博杂,而且在于六艺之学不切实用,又为后代学者所牵强附会。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由儒而墨,创为新说,这都充分说明到战国之际,以六艺之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发展到了非变化不可的程度。因此,诸子百家的兴起,是对六艺之学的新发展。而《左传》、《国语》记春秋历史,也正是不满足于《春秋》之简略。没有《春秋》,起码可以说没有今日之《左传》,但没有《左传》对《春秋》的发展,也不合于文化发展的需要。战国历史散文,也正是采纳了六艺之中记言、记事史书的特点,而加以发展的。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王道微而诸侯为政之时代,即周道大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的时代,这个时代居于春秋之后,称为战国。荀子、屈原辞赋继承古诗传统,而宋玉、唐勒则更多表现为新变化。
关于战国文学对六经的继承与发展,刘勰说得非常清楚。《文心雕龙·辨骚》论楚辞与六经异同,有相同者与不同者,曰: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龙凤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
屈原的作品,其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同于风雅,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异乎经典。是以六经为典范,而又杂战国时代精神之作。作为词赋之代表,比之经典则博杂。其义则取自经典,其辞藻则来自自创。
又《文心雕龙·诸子》论诸子与六经之不同曰: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军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鸮鸟,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
战国诸子与六经,也是有同有异。其同表现为继承,其异则表现为创新。
战国诸子、辞赋之外,又有历史著作如《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论《左传》与《春秋》之区别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又《汉书·艺文志》云:
周室既微,载藉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设若《左传》确实与左丘明有关,并为传《春秋》之作,在思想内容上,它也是改孔子之隐晦委婉而为直截了当,其批判大人君臣,而不为隐讳,其敷衍本事,有“浮夸”之“诬”。
战国文学与六经的差别,可以概括为“奇诡辩丽”四个字。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楚汉侈而艳。”这里所说的楚,即战国屈原、宋玉、景差等人的辞赋。屈原、宋玉、景差之辞赋,以华美而奇特的形象,艳丽而充满神秘色彩的意境,优美而缠绵悱恻的音节,独树一帜的以楚地方言为特征的语言,形成一种与典丽文雅的文学传统迥异的新风格,刘勰以“侈而艳”来形容。又《文心雕龙·辨骚》肯定楚辞具有“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瑰诡而慧巧”,“耀艳而深华”之特征,感叹其“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时序》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刘勰这里一方面肯定屈宋之辞赋有超越《诗经》之艳丽,同时,又认为楚赋炜烨之奇,受纵横家的诡俗影响。也就是说,刘勰不仅认为屈宋之辞赋是艳逸、炜烨,奇丽谲诡的,纵横家之说辞也是充满了诡瑰风貌的。而纵横家的说辞,既体现在诸子散文中的纵横家类中,也体现于诸子百家中其他出身游说策士的著作中,而史传散文描写的游说之士的游说之辞,更是充满了奇谲诡瑰特色。《文心雕龙·论说》云:“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等人,学鬼谷子之术,其诡辩巧辞,已至极致。其事并见于《战国策》中。这种对诡奇、艳丽、辩雕、藻采的追求,是一种对艺术美的追求,是文学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体现在战国楚辞楚赋之中,也体现在战国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之中。既是一种艺术特征,也是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出的新特点。
战国文学作品既以奇诡辩丽见长,战国文学家的行为也充满奇异色彩。孟子的执着,庄子的疾愤,杨朱的偏激,墨子的自苦,鲁仲连的清高,苏秦、张仪的辩洽,自有其不凡的魅力。而屈原遭世罔极,怨恶愤怒,九死不悔,终至沉江,更有一种神奇。
相对而言,孔子的行为则透露出更多的恬淡。
董仲舒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以深切著明的行事,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孔子作《春秋》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神圣使命感,与屈原之作《离骚》,其机缘动机很有接近。孔子周游列国。百折不回,欲力挽狂澜,却处处碰壁。当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之际,知天命之不至,感叹曰:“天丧予。”曰:“吾道穷矣。”曰:“莫知我夫。”涕泣不已,但却能“不怨天,不尤人”,“不病人之不己知”,而知所已。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又对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说伯夷、叔齐曰:“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主张生存的智慧,严格要求自己,而通达地恕人,己所不为,则不施于人。赞扬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不死,却有利于众生,这便是其价值所在,人之生命可贵,岂可以死而无悔?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绝不在乱世求不义富贵,所以赞扬学生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而以其兄之女妻南容。《论语·泰伯》更是详细地阐述了孔子的处世智慧,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卫灵公》孔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述而》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子路》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颜渊》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孔子处世,首先要判断身在治世,还是身在乱世,治世则仕,乱世则隐,不入危邦。不伐己功,如舜、禹之有天下。不争不党,矜持自尊而团结群众,可与言则言,不可与言则不言,道不同则不共谋。保持坦荡之胸怀,因而可以不忧不惧。孔子教导其弟子子夏为“君子儒”,而不为“小人儒”,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处乱世, 守死善道,无疑便是君子儒的榜样。屈原身处乱世,不欲明哲保身,与时抑扬而好修为常,自负其能;欲以忠贞立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甚至以自杀来证明其清白,反圣人之所为, 可以称为千古至奇之人。也正是有了战国时代文学家这奇诡,因而才有战国文学之奇诡;因为有了以辩丽为能的战国文学家,才能创造出文学的辩丽之美。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自春秋战国,就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尊重,这种尊重,绝不是没有原因的。通过对孔子与战国文学繁荣的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从而全面、深入、充分地了解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历史地位。
【编辑:宫英英】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
- 让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中华大地持续迸发
- 文化“两创” 时代华彩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蔡先金: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 尼山讲堂丨杨传召:《中庸》通讲(三)
-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成都进行友好交流,从都江堰治水之道悟治理之道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 当千年漕船驶入“数字星海”
- 齐鲁大地吹拂文化“两创”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