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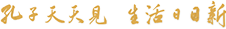



-

孔子网客户端

中国孔子网微博

中国孔子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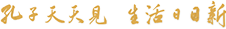




孔子网客户端

中国孔子网微博

中国孔子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关于国学的概念问题关于国学的概念问题,究竟哪些是国学,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其他的都不能算国学。这是一种概念,这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概念。但是我觉得,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国学要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门专门学问,固守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实际情况了。我们56个民族,汉族的文化当然居主流,但是我们还有兄弟民族的文化。我们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
所以我借用北大一位哲学家张岱年讲过的,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因为是我们国家以内的。国学是区别于另外国家,以这个作为概念,我们应该是包括一切学问。当然他的意思是国学里可以分主次,但是不能排斥我们自己的长期以来,多少民族合成的许多学问。原先西域学也不包括在里头,但是王国维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西部的研究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西部的简牍,还有斯坦因等早期盗取的大量西域文书。但是从王国维到现在多少年了,尤其1949年以后,我们西部出土了大量古代的经典,因为出土在西部就不算我们的国学?那当然不能够这样。而且我们进入西部也是很早很早的,中国的西部历史也是很悠久的,西部的民族跟我们的融合也是很早很早的。

冯其庸在卡拉库里湖和慕士塔格峰前,1998年摄。
比如我在吐鲁番阿斯塔娜古墓看到好多幅伏羲女娲的像,就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作品,都在墓里出来的,因为那地方干燥,没有损坏。其中有一幅画像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就是伏羲像有两撇小胡子,戴一个小帽子,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维族的人也把我们的创始神伏羲女娲作为他的创始神。这说明我们的汉族文化跟少数民族兄弟文化的融合已经很早很早了,这是我最早发现的,我去看了以后,我一下感觉到这个太有意义了。
据我记忆,像阿斯塔娜古墓里,这样的带有兄弟民族特色的伏羲女娲像,就有两幅。这批画没有都展出来,只展出一幅。我看到展出来的这幅,发现了这个现象,我一说以后,他们又从没有展出的里头找到了一件。
后来他们告诉我,库车也有一幅留着小胡子,戴着小帽子的伏羲女娲像,再次证实了这个创始祖的神话已经被我们兄弟民族维族认可了,而且认可的时间不是后来,是魏晋南北朝到唐,那是够早的了。我分析,兄弟民族把伏羲女娲作为自己的创始祖和它在民间流传的时间,应该比这几幅画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所以我们今天来重新整理国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一个大的范围概括进去呢?
所以我就提出来一个“大国学”的概念,要把我们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也吸纳到国学里。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国学就是新国学》,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
西域研究所的建立基于我的“大国学”的概念,我跟季羡林先生商量,我说要给中央写封信,建议在国学院成立西域研究所,把西域学通过正规的建制,纳入到国学的范畴里,这是“大国学”概念的具体实施,季羡林先生也非常赞成。他让我来起草,成稿后打印好了,我就请季先生一起署名给中央上书。我把我打印好的稿子我先签好名,在我的名字前面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白,好让他签名。结果,他拿去一签,签在我的后头。我说你应该签在前头,你签在后头,后头就剩下那一点空缺了,太挤了。他说,你在国学院担任院长你当然应该在前头,我放在你后头才合适。后来没有办法,因为亲笔签的名,这样这封信就送到中央去了。我在罗布泊帐篷里的时候,中央台的同志就跟我说,现在卫星电话安排好了,你要不要给北京通个电话?我就在罗布泊帐篷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一打电话,夏老师就告诉我,她说你们的报告胡总书记已经批下来了,同意成立西域研究所,而且还批了四千万创办的经费,先拨了一千万,其他还保留在我们的名下,需要用的时候可以用。
中央批准了在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西域研究所,我们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我们把原来新疆考古所的所长王炳华请到国学院来了。
我们又从德国请回了沈卫荣,沈卫荣虽然年龄不算太大,但是他精通西域各种中古的语言,尤其精通古藏文。因为这些语言已经是死语言了。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唯一一位精通中古时期西部语言的老前辈,他带出来好几位有突出成就的学生,足以继承季老的绝学。而沈卫荣同志,就是专研西部中古文字的专家。他一直在德国,是国外的西域研究的一面旗帜。有人建议我,把他请回来,而且他一回来,加上季老培养的学生,那我们的西域学就会兴旺发达了,西域学的研究重点就移到国内了。

汉玉门关夕照,2005年摄。
所以我们就想法子跟沈卫荣先生沟通,我就说你在国外的所有的条件,不变,只要你回来,回来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你在海外看到的许多资料,都是以前流散出去的,1949年以后国内发现的有关资料,就再也不会流出去了。所以我说,你在国外这么多年,斯坦因他们那批资料你都很熟悉了,那么新的资料你没有机会看到,你只有回来才能看到。他一听就非常高兴,就马上答应回来。回来到我这里一碰头,才知道我们还是老乡,他也是无锡人。非常高兴,特别是说到,建立西域研究所要把这门学问传承下去,而且得到党中央的关注,所以他也非常愿意。
两年中,我帮他们制定了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师资的聘请,同时成立了西域研究所。
我们正式成立了西域研究所。当时也计划要成立汉画研究所,但是由于人手不够,力量不够,至今没有成立。
从国学院的角度来讲,我们成立了西域研究所,目的是要把西部发掘出来的许多地下资料整理、研究。另外西部的发掘在一百年前斯坦因他们已经抢在前头了,那个时期出土的一些资料,都被他们拿走了。但是,因为时间毕竟经过了一百年了,他们也陆续都整理出来公布了。1949年以后,我们有更多的发现,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管理也严密了,我们出土的东西,除了有少量被偷盗出去以外,正式的公开渠道都不能出去了。因此我们后来发现的许许多多重要的原始资料,都不传到国外去了,都是首先由我们研究出成果来公布。我们国学院编了一部吐鲁番新出土的文书,都出版了。
从国学的概念来讲,西部地区出来的许多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物,当然在我们研究范围以内。另外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兄弟创造的文化,也是我们祖国的文化大家庭里的一份重要的财富,我们不能把它抛弃。所以我们创立西域研究所,从文化角度来讲也是实现“大国学”的概念。

以上文字、图片来源:“商务印书馆”公众号,摘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