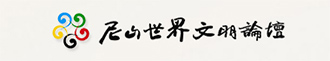期刊精粹 | 余治平 | 调均:以社会分工制衡财富分配——董仲舒“仕则不稼”、“天不重与”的政治哲学
2025-12-15 11:48:04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余治平
汉兴六十多年,朝廷实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在获得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董仲舒向武帝所上《天人三策》列举出当时贫富悬殊、利益不均衡的种种现象:“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权贵豪门富可敌国,经常拥有数量可观的奴婢,牛、羊等牲畜以及田地、房宅都难计其数,而贫困的人则穷急愁苦,没法存活。一富一穷,两极分化,反差巨大,如果再不设法缩小二者之间的距离,一切现有秩序又将打乱重组。这无疑是帝国当前急需解决的第一问题,也可以说是武帝一朝“最大的政治”。面对这一紧迫的时代课题,多数儒者主张向先圣祖宗寻找药方——实行井田制,而董仲舒则试图从社会分工(包括行业分工、阶层分工)的角度切入,在源头上调节、规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流向,以达到制衡的效果,进而使他所提出的“调均”方案更趋前瞻性。
一、“仕则不稼,田则不渔”
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要尊重社会分工,体恤底层民众,不剥夺他们的职业权利,做到不与民争食,不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这里的“君子”应该看作是社会管理者或脑力劳动者,而具体的体力劳动者则是“小人”。君子位居社会上层,管理别人;而小人则处在社会底层,被人所管理。百工“小人”可以追逐利,而上层“君子”则应该不沾利。一国之内,如果官僚阶层时刻算计着老百姓的口袋子,争相盘剥民众的利益,那么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宋儒程颐说过:“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这里,“深耕易耨,播种五谷”是农民的分内事,作为“百工”就发挥自己的“技艺”而制造出“器用”,而“甲胄之士”的职责就在于“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君子只要“食之”、“用之”、“安之”就可以了,不必亲自去劳作的。君子也有属于自己的职业,不过他的职业并不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之类的一线生产岗位上,而在庙堂之上,而在运思之间。君子的一个善念,君子的一句人话往往都会对底层百姓发生命运攸关的决定作用。
《礼记·坊记》假托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郑玄《注》曰:“不与民争利也”,孔颖达《疏》曰:“言君子不尽竭其利,当以余利遗与民也”。君子不尽取物利,必须留有物利给民众。郑玄《注》与《坊记》原文、孔颖达《疏》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不尽利”,或可说明官是可以与民争利的,只是不要太黑就行,手下留情,征收各种税费赋敛,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人性化执法,而不能太无情,不能赶尽杀绝,给老百姓留点活路,不至于使他们造反。“不尽利”是程度问题,民脂民膏还是要搜刮一下的,只是要注意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突破底线,不能滴水不漏而让他们活不下去。而“不争利”则要求一点都不能与老百姓抢饭碗,官是官的,民是民的,界限森然,不可跨越。“不争利”是原则问题,钱财面前,当官的就是要让步。官府只管政治局面,主持公正,维护公平,而不应该计较自己的经济得失,更不应该插手某些行业或某个行业的利益分配。在任何时候都绝不允许发生当官的从老百姓口里夺食的现象。
利益面前,老百姓无疑是抢不过当官的,就因为后者手上持有特权,可以肆意干涉许多行业的正常运营,操控其价格,把持并垄断其利润,让别人无法与之平等竞争。“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说明官府垄断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只是强调要有对百姓利益在程度上的正视、保护与留存。而“不与民争利”则根本就不允许侵害百姓的基本利益,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吕祖谦说过:“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士大夫领取俸禄,就不应该再图利,行仁践义而已,这是儒家典型的君子要求。一旦士大夫无耻,就会国将不国了。
《度制》篇引《诗》曰:“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应该是今本《诗经·小雅·大田》“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之误刻,当是《齐诗》、《毛诗》流传之衍异。“穉”,通“稚”,指幼禾,没长熟的庄稼;不获稚,指晚种而后熟的庄稼。秉,即把、握,引申为田间稻、麦收割的数量单位。穧,指庄稼倒地而没被捆扎。《大田》的这段文字之前,其实还有一句:“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里,“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而同养公田也。”郑玄笺曰:“古者阴阳和,风雨时,其来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后私,令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尔。此言民怙君德,蒙其余惠。”周初之时,天下太平,世道和洽,即便云兴雨落,往往都是先浇灌集体的公田,然后再滋润每家每户的私田。君王收缴赋役,没有竭泽而渔,而是让他们也能够有利可图,享有一定实惠与便利。所以,郑玄笺曰:“成王之时,百谷既多,种同齐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获、不敛,遗秉、滞穗,故听矜寡取之以为利。”
儒家之治理不仅一直强调修身养性,注重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求匡扶天下,经世济民,始终致力于让社会成其为社会。《论语·宪问》所载孔子所谓“修己以安百姓”,即是后来的内圣外王之道,谓君子要在“修己”与“安人”、“安百姓”两个维度上同时下工夫。既然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就必然要维护一个错落有致、和谐安宁的生活秩序,积极关照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因素而落魄困苦的弱势群体,主动调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一种有差别但无对立、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礼记·礼运》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作为君王,最理想化的善治就是要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生活目标而有序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但是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个前提,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君王要带头遵循并力行儒家的恕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率先做出榜样,感染治下的每一个人。最终,照顾鳏寡孤独的责任便又戏剧性地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任务分解,化整为零,还是发动社会力量进行扶贫问苦。“既四海如一,无独其亲,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赡养,终其余年”,君王无论如何是甩不掉自己肩上体恤贫寒、抚慰鳏寡的义务的,如果总要求天下人“无独其亲”而“赡养”弱势群体,那么,设立君王这个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究竟还有什么用呢?!
在《度制》篇中,当董仲舒明确要求“君子仕则不稼”的时候,他所坚持的肯定是“不与民争利”的态度,而不会是“君子不尽利以遗民”。“稼”的含义是播种五谷,种庄稼原本是农民做的事情。官员在官言官,以做官为自己的职业,而不应该再去兼做农民的事情,去赚本该是农民赚的那份钱。不同职业之间,应该确立一系列的领域边际与利益界限,清晰而明了,而不致相互交叉、彼此打架。本行业的事情不好好做,手伸得太长,贪心不足,兼取得太多,最终则必然什么做不好。周桂钿指出,“一个人不当得两方面的利益”。所谓“并兼”,就是指“同时兼得多方面的利益”。而这恰恰是一种违背“分予”原则的不正常现象,必须尽力加以制止和反对。
实际上,“仕则不稼”的命题里还隐含着掌握特权、控制社会资源的官僚集团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垄断、霸占与褫夺。而这又远远超出了不同民生行业之间的利益交换与兼取,因为官府与民生行业之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当前者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优势、运用手中掌控的特权对后者形成一种强迫和威逼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财富都会无条件地汇聚和集中到他们手中,这就出现了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对称,其后果通常是官府富得流油,特别是朝廷,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中央财政总有用不完的钱,而民间则积贫积弱,不堪一睹。富国穷民,肯定不是儒家一向所倡导并追求的善治。其实,政府太有钱,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当公职人员并不具备合理支配公共财富的德性和能力的时候,反倒会大面积地激活、助长原本一直潜藏在他们身体内的那种贪婪、自大、狂妄和戾气。于是,政府太有钱就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所以,不能把“仕则不稼”看做简单的那种隔行取利,其实它远比一般行业的不正当经营更有危害,必须引起高度警戒和密切注意。
“田则不渔”要说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尊重社会分工,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自己不会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然后必须自愿地、主动地把它们让渡给别人,并且相信别人能够做,会把它们做得了、做得好,而自己则在自己所选择的行业领域里安身立命,发家致富。进而,划定职业边际与经营领域,不鼓励不同职业之间交叉相兼、互抢饭碗,不主张隔山取利,妨碍别人的财路。与“田则不渔”相对的则是“渔则不田”,种田的就种田,打鱼的就打鱼,这样才能把各自的事情做精做好。如果种田的也去打鱼,抢了打鱼的饭碗,你让打鱼的怎么活呢?!反之亦然。不同职业,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彼此尊重对方的专业领域和行业范围,才能促进物资生产和贸易流通,实现价值交换和利益共享。
二、“天不重与”: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古往今来,人类的劳动行为及其所寄托的组织形式,专门化、专业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这是规律,不服是不行的。产业分工或行业分工虽然是社会性的,必须由人来执行和操持,但在本质上也近乎一种天然选择,必须被尊重和确认。而且,分工本身还在不断进化,越来越精,越来越细,现代化运动之后,许多职业被精细化,传统的一级行业往往催生、滋生出更多的二级甚至三级、多级行业,机械、电子产品的一个元部件甚至都能够撑得起一个完整的行业。于是,又会出现一种整合、协调不同行业的趋势,以集聚力量解决更大的发展问题,防止因为过分精细化而导致的分工瓶颈和行业钳制。
在董仲舒看来,“仕则不稼,田则不渔”的逻辑原因与天道根据则在于:“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春秋繁露·度制》)董仲舒思想与学术的一大明显特点就是,每每议论现实事务与问题,都要从玄虚的天道那里寻找根据,然后再展开一番严密的逻辑演绎和学理论证,所以他得出的结论一般都经得起来自形上与形下两个方向的拷问。显然,“仕则不稼,田则不渔”已经被他上升到天道逻辑的高度来予以认识和理解了。官不与民争利、尊重社会分工的终极性缘由只在“天”上,而不在尘世中,从人类自己身上及其活动中所寻找到的所谓“原因”都不足以成为根据,最多只能算作现实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已。
一句“天不重与”,就反映了人类分工形成和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上天是不会重复赐予或同时赋予某一个动物两种或多种独特的生存技能的。因而上天是公平的,它在创设万物之初就已经考虑到各自的技能优势和存在领域了,已经为每一个物种划定了主要属于它自己的生存能力、活动范围与获利空间,以使它在这些方面与别的物种即便有交叉、交往而不至于相互打架和彼此伤害。天有所“与”是正常的、应该的,但“重与”则属于兼得,是贪多,客观上会挤压其他存在者的存活空间,因而都不能为天理所容。按照董仲舒的生物学理解,“有角”的动物绝不会再有“上齿”,反过来,有“上齿”的动物也绝不会再“有角”。在动物世界里,某种动物身体某个部位的功能过分发达了,其他部位的功能也就显得相对平庸。在同一种动物的身上,不可能所有器官的功能都很强大,优势不可能获得平均分布。
所以,在董仲舒看来,拥有“大者”便一定不能兼得“小者”,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天数”。而如果哪种动物违背自然规律,一方面拥有“大者”,另一方面又要兼得“小者”,连上天都不可能满足他的贪欲。动物界如此,人间的事情就更是如此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反过来,已经有“小者”能不能兼得“大者”呢?董仲舒并没有提供明确的阐述和分析,原因估计是,“小者”兼得“大者”的可能性极低,即便偶尔发生,也肯定不容易,所以就没有必要再作为单独的问题而予以突出和强调了。大者兼小,轻而易举;小者兼大,非常艰难。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中,要想形成“上下相安”的和谐局面和天下稳定的一统秩序,不断对权贵阶层加以约束,经常对强势群体加以抑制,始终都是最高统治者所必须面对的急务,毕竟,上层波动比底层骚乱处理起来要麻烦,也更让人费心。这样,防止“大者”兼得“小者”,要远甚于防止“小者”兼得“大者”。
如何限制官与民争利是古今政治统御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一大难题,也是许多儒学思想家所关注的核心政治哲学问题之一。在总体方向与基本要求上,儒家一直既反对官与民争利,又反对官与民争业,而始终强调官是官、民是民,官之职事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因而只追求公平正义;而作为百姓则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公开追逐利益。与历史上中国官僚政治所呈现出来的动辄垄断国计民生产业的许多铁腕做法大不相同,一向具有仁道情怀的儒家并不主张权贵士族、大夫阶层涉足民众营生,以赚取百工之利,并且以这种行径为羞愧与耻辱。只有明确阶层分工,划定阶层从业的边际范围,才能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社会财富的流向,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病症。君子不干小人之事,小人也不登君子庙堂,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各自收获自己应该得到的回报,天下秩序才能稳固有伦。
在回答武帝的第三次册问时,董仲舒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上天最初在创造每一个动物种类的时候,考虑得已经很周到了,公平对待,分配得当,因为它是按照每一个动物种类的名分、本分而分别赐予一定的价值、功能和特征的。所以“天亦有所分予”这一点,跟《度制》篇“天不重与”的立场是完全相统一的。
至于“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及其理由:“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更与《度制》篇“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的文字高度一致。齿、角不两有,翼、足难齐全,这在《淮南子》、《大戴礼记》都有类似的文字记载或描述,据王先谦的判断,它们可能皆“祖仲舒之意”,甚至直接就援引于董仲舒的文献。《淮南子·地形训》曰:“万物之生而各异类。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介鳞者夏食而冬蛰,啮吞者八窍而卵生,嚼咽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指而无后。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差异化选择是天地万物生成、存在的最基本法则。一物有一物的身体机能、形态特征和活动方式、作用范围,不能轻易用一物取代乃至取消另一物。卢辩注《大戴礼记》引《淮南子》曰:“蚕食而不饮,三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饮不食,三日而终。”蚕、蝉、蜉蝣,各自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它们汲取能量的渠道、它们的生命周期也不尽相同。介鳞者、啮吞者、嚼咽者之间的差别亦然,都理当获得尊重。“无角者膏而无前”中,膏,豕也,即猪,“熊、猿之属”;“无前”,“肥从前起也”。“有角者指而无后”中,指,“牛羊之属”;无后,“肥从后起也”。《说文解字·肉部》曰:“戴角者脂,无角者膏。”《一切经音义》引《三仓》曰:“有角曰脂,无角曰膏。”而“无前”、“无后”,于义似乎不顺,刘文典说:“义不可通”,因而怀疑“无”是讹刻,当作“兑”,“无前”、“无后”应为“兑前”、“兑后”。因为“豕马之属前小,牛羊后小”,所以“前小即兑前,后小即兑后也”。
《大戴礼记·易本命》曰:“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又,“有角者取前齿,有羽者无后齿。”成书稍早于董仲舒之世的《吕氏春秋·博志》也说过:“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无遂功,天之数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这里,同样也把“有角者无上齿”,作了一个普遍化的提升,用的是一个全称判断,并且以之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则,是“天之数”。如果说《淮南子》、《大戴礼记》直接援引了董仲舒的文字,似乎还有可能,但完成于秦统一六国前夕的《吕氏春秋》,则也有可能成为后世董仲舒的思想来源。看来,齿、角不兼,翼、足难全,在汉代已经是一种流行而普及的“科学观念”,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难道上苍在创造地球动物界的时候真的是“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吗?说“傅其翼者两其足”,似乎还情有可原,因为今天人们所常见的飞鸟都是有翼而两足的,两翼又四足之类的史前动物则早已灭绝,只有在化石考古或神话传说中才出现过;但说“予之齿者去其角”,则很容易被证伪,有齿又有角的反例并不鲜见。如果谁真的相信了汉代书籍里的这种“生物学规律”,硬去验证于常见家禽牲畜,扳开它们的嘴巴一瞧,那肯定是要失望的。所以,王先谦便指出:“此非通论也,其他羊、鹿之属,岂皆无上齿乎?!”这种生物学规律并不具有什么绝对的普遍意义,而只体现在某些甚至个别动物的身上。
但问题是,在农业文明的时代里,自然生态环境保存得还算相对完好,羊、鹿以及牛之类的家禽,几乎随处可见,它们既有上齿,也有角,但为什么汉代这些著书者偏偏说齿、角不能两全呢?难道他们都在睁眼说瞎话吗?王先谦的解释是:“牛善触以角为用而无上齿,若羊、鹿之属虽有角又有上齿,然角不为力用,非牛之比。斯言亦就物理参悟,无取拘牵古义,相承由来已久。”但是,仅从动物身体的用力部位的差异性和局部功能的优先性来解释,似乎仍不能够说服人。牛角有力,其上齿同样也有力,否则,它就没法把地上的劲草硬生生地拽到自己嘴里来了,也没法把那些坚硬的植物咀嚼得细碎。羊、鹿有上齿,但它们的角同样也很有力量的,否则,它们靠什么跟同类抢食,靠什么去抵抗天敌呢?!不过,按照王先谦的解释,齿、角不两有,翼、足难齐全,这种说法领会一下就好,其科学性与真理性只在“物理参悟”时有效,不必“拘牵古义”,更不必细挖深究,就权当“相承由来已久”的一种习惯性说法罢了。
显然,与《度制》篇一样,《天人三策》里大讲所谓“予齿去角”的生物学规律,其潜在意旨不是真的要向今人传播或普及那些汉代自以为是的自然科学知识,毋宁要阐明权贵阶层“不与民争利”的社会道理,借助于天道揭示人道,才是真意和底牌,因而也会获得更强大的诠释力和说服力。“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显然,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吃皇粮的与靠手艺养家糊口的从来都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拿政府俸禄的就不应该再靠出卖体力而生存,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不仅古代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还是如此。当官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立足好本位,不觊觎别人赚钱,不眼红别人发财,而必须做到不稼不穑,不做农民做的活儿,也不去从事工商经营活动,与工商界争利。“末”,颜师古曰:“谓工商之业也”,它是相对于官员本职、本位而言的。从体制内获得稳定的生活资源,显然是得了很大的好处,因而就应该放弃细小的利益,完全没有必要跟市井小民去抢饭碗,更不能狗苟蝇营,丧失廉耻。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也是把这个要求上升到“天道”逻辑的哲学高度来看待的。无论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存在物,还是对于群居的人类,“受大者不得取小”,天意就是如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可商量。
“已受大,又取小”,豕心不足,贪欲太盛,这往往也是天下老百姓生活凄苦、民间社会充满冤愁的主要原因。对于权贵阶层而言,你们出身于荣耀的门庭而又在官衙里占据着重要的职位,拿着丰厚的薪水,这还嫌不够,仍然凭借手中掌握的财富与人脉资源而跟那些整天在田头上、市井里靠出力流汗才能够养活自己的老百姓们争利益、夺钱粮,这叫他们怎么活啊?!弱势敌不过强势,他们哪辈子才能赶得上你们,过上你们的生活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先天的不平等只有靠后天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予以适当的弥合和补齐,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知识精英分子中的精英,圣人的价值和作用便开始凸显了出来,因为在一个浑浊不堪的社会里,也只有这一帮不当权、不沾任何利益的清流,才会出于最基本的公心和道义而设计出一套制衡系统,调节贫富,填平余缺,以维持天下秩序的稳定。
三、“受禄之家”当“不与民争业”
因为阶层分工而导致的贫富差距,也不可忽视。《春秋·隐公五年》载:“春,公观鱼于棠。”《穀梁传》称:“非常曰观。”《公羊传》则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事见《左传》,“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诸侯非王事则不出,非民事则不出,《春秋》用讥辞,意在贬抑隐公无事而跑出都城,“慢弃国政,远事逸游”,显然是“纵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礼也”。君王慢政,则是国将有祸的征兆。《春秋繁露·玉英》篇中,董仲舒曰:“公观鱼于棠,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人性之中,原本蕴藏着善义因子,往往都是利益诱惑而使人学坏作恶,君王、凡夫皆难克服。何休《解诂》也直指隐公“去南面之位,下与百姓争利,匹夫无异”,因而是君王的一种耻辱。《春秋》书以“远观”,乃孔子讳大恶之辞。
与《度制》篇“天不重予”的观点相一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也指出:“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显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的要害看得很清楚,抓得也很准确。天下“利可均布”、“民可家足”的前提是:“不与民争业”。作为“受禄之家”,既然已经从官府那里领取了俸禄,就应该借此为生计,不再僭越本位而染指别的行业,与下民争利。只要权贵阶层不涉足民生行业,那么天下的利益就可以获得平均分配了,老百姓也就能过上富足幸福的日子了。当官的“不与民争业”,这是一条发自上天而又经过历史检验的铁的法则,既具有先天必然性,又具有客观现实性。所以,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就应该按照这一法则而建立和完善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作为社稷之臣的大夫权贵阶层更应该无条件地把这一法则落实于自己的行动之中。
“公仪子”,颜师古曰,即“公仪休”也,是春秋时期鲁国穆公时的博士官,司马迁在汉初撰写《史记》的时候把他收进了《循吏列传》。其文曰: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这里提供的无疑是“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的一个典范案例。公仪休之为官,“奉法循理,无所变更”,显然属于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那种官员。不收贿鱼,足以说明他脑袋清醒,担心“受鱼而免”职,害怕因为贪图小利而丢掉一国宰相的饭碗,一般的声色货利根本是不足以打动他的,可见他绝非一个见利忘义之徒。而拔葵、去织两事则是“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自规律条的最好注释。当官的人家,如果什么东西都自产自用,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那么,问题来了,农民地里生产的粮食、蔬菜和水果,商贩手中经营的商品货物,还卖给谁呢,这叫他们怎么活啊?!对于位居社会上层的权贵显达人士来说,对于社会底层某一具体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不该你做的事情,你就别做;不该你赚的钱,你就别赚。越位兼利,鸠占鹊巢,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没能体现天道规律,是社会无序的标志,必须及时予以纠偏。
公仪休的这一佳话后来便成为世代流传的典故,经常被省略为“拔葵去织”,或干脆简称作“拔葵”,意指居官的食禄之家不应该与民争利,不能抢老百姓的饭碗,所强调的都是,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不能贪心太重,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势力量,而侵占弱势群体的利益,导致直接或间接威胁他们的职业,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杨树达说:“武帝他日兴利之政,仲舒盖早有所窥见,故其言如此。”这是董仲舒对武帝朝政的批评。
而从社会分工的层面看,士、农、工、商四大职业各有所司,各有所能,不同的人从事着不同的生产,领域差异决定着地位、回报、收入的不同。四大职业之间,有交叉但却不打架,各自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而购买其他职业的劳动和服务,互通有无,由此而推动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些都是平民百姓的营生,是他们的饭碗,所以才称为“庶人之业”,位居社会上层的权贵显达一旦插手进去,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为权贵显达掌握和控制着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很容易形成垄断,普通百姓是没法跟他们竞争的,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四、“居君子之位”不可“为庶人之行”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不仅呼吁君子贤人阶层必须保护底层民众的基本利益,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上层不贪婪、不多取对于底层百姓的号召、引领作用和风俗教化的意义。“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并引《诗》讽刺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可见,“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又引《易·解卦》六三爻辞曰:“负且乘,致寇至”,意欲表明“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类似于公仪休“拔葵去织”之事,上古时代比比皆是,居于社会上层、有身份有地位的贤人、君子也大多能够做到。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就会认为贤人、君子的言行很高尚,值得尊敬,然后就会纷纷效仿、学习。进而,这些老百姓也就跟着要求低而有节操,不会贪婪无厌,也不会卑鄙地去作践自己。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政风,就有什么样的世风,这就叫做“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然而,到了春秋之后,王室衰微,诸侯当政,道义心荡灭而利益心充斥于天下。再往后来,卿大夫篡权,执令行事往往放松道义原则要求,却不断追逐利益,疏于尚义而乐于趋利,完全丧失了上层贵族所应当具有的那种推辞、谦让风范,有身份的人不断为争夺田地以至于诉讼不绝,导致世风日下,民心衰坏。
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其职责和使命显然不同于底层百姓。在董仲舒看来,整天“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一般的市井凡夫,他们始终被巨大的生存压力所逼迫,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日不劳作则一日不得食,所以总表现得非常急切而惶恐,丝毫不敢苟且、偷懒。在这个世界上,唯独他们可以整天把金钱利益挂在嘴边,唯独他们可以整天把生意活计粘在手上,否则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靠老百姓缴纳财物税赋而养活的皇帝老子、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则应该同样非常急切地为整个社会确立起仁义旗帜与理想,经常焦虑并唯恐自己不能够教育、感化天下百姓,使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这才是他们的正事儿。“庶人之意”肯定不是“大夫之意”,“大夫之意”也肯定不是“庶人之意”。庶人可以在内心燃升起“大夫之意”,位卑未敢忘忧国;而大夫却不可以萌生出“庶人之意”,灵魂深处断此念,不可以自甘沉沦。如果一旦在概念上有意、无意混淆两者,则无异于为权贵阶层褫夺百姓利益提供机会和开脱罪责。
面对武帝朝贫富悬殊拉大、两极分化严重,以至于阶层撕裂、民不聊生的危急形势,董仲舒敢于对武帝直言不讳,劝谏匡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其勇气非常值得肯定和钦佩。总体上看,董仲舒提出的“调均”理念是具有系统性的,从土地政策的“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到税收政策的“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再到人口政策的“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还有打破国有垄断的“盐铁皆归于民”,等等,另有专论。本文仅仅从社会分工(含行业分工、阶层分工两大方面)制衡财富分配的视角而予以分析和诠释。华友根对董仲舒的调均思想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武帝时的主张、作为,无人可及。丞相公孙弘根本不能跟他比”,“公孙弘元光五年的对策策文,不能与董仲舒元光元年对策所谓‘天人三策’相比,还停留在战国中期孟子的‘四端’。”所以,“董仲舒不是一般的政治思想家,而是超过前人与时人的大政治思想家。”而董仲舒对分工与财富分配的关联性分析,切入点显得非常独特,也颇具睿智,看得准确,能够击中问题的要害,进而,非常有效地把对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危机的探讨和研究引向深入。
【编辑:张晓芮】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开放日,遇见革故鼎新的新山东——山东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侧记
- “十问十答”,山东之变有新意更有深意
- 韩正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 奋进“十五五” 勇于挑大梁——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为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指引方向
- 政府工作报告极简版来了!不到1000字
- 凝聚人心 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开幕侧记
- 尼山讲堂丨魏衍华:《中庸》通讲(十三)
- 习近平总书记向女同胞致以节日祝福和美好祝愿
- 开放日,遇见革故鼎新的新山东——山东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侧记
- “十问十答”,山东之变有新意更有深意
- 直播丨尼山讲堂:魏衍华《中庸》通讲(十三)
-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举办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暨孔子学堂公益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