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2017-05-17 09:33:00 作者:何兆武,邓京力 来源:
何兆武:我只是自己对此有兴趣,我是尽量淡化自己,边缘化。真正的主流,比如近代几位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后来的胡适。有的人就很难说了,究竟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很难说。你这么说,让我无地自容了。
访问者:您太谦虚了。您翻译和评价了克罗齐、柯林武德、沃尔什的著作,特别是对波普尔? 历史主义贫困论? 一书进行的评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何兆武:其实那篇文章写得非常不好。因为波普尔是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的,所以写的时候有框框,一定要批判他。其实他那书里面有些内容我不赞成,有些还是讲得很不错的,可是关于他讲得很不错的那部分我就都没提。
最近我还要写一篇小文谈这个。我最近看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就是曹汝霖的回忆录。五四的时候要打倒的头一个“卖国贼”就是曹汝霖,火烧赵家楼就烧的是曹的住宅。他的回忆录后来在台湾出版的。他写了很多,有些东西很难讲是对是错。照他自己讲,他一点都不卖国,是非常爱国的。我想也有个证明,就是日本人来了,他住在天津,日本人组织伪政权叫华北临时政府,叫他出来担任傀儡政府的委员长,他不干。后来日本人才找了王克敏,王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第二次改组成华北政务委员会时,又要他出来,他也不干。第三次组织华北联合准备银行,说这不是政治,他也没有出来。我想这个毕竟是事实。所以一个人究竟怎么评价也很难说。他要是出来任职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他是三个卖国贼里的第一号,但他没有担任,这如何解释? 可见知人之难。
吴佩孚也没有出来,吴佩孚死了之后,国民政府还有一个褒扬令,做了汉奸就不能褒扬了。汪精卫年轻时是很革命的,结果汪精卫做了汉奸了,确实也很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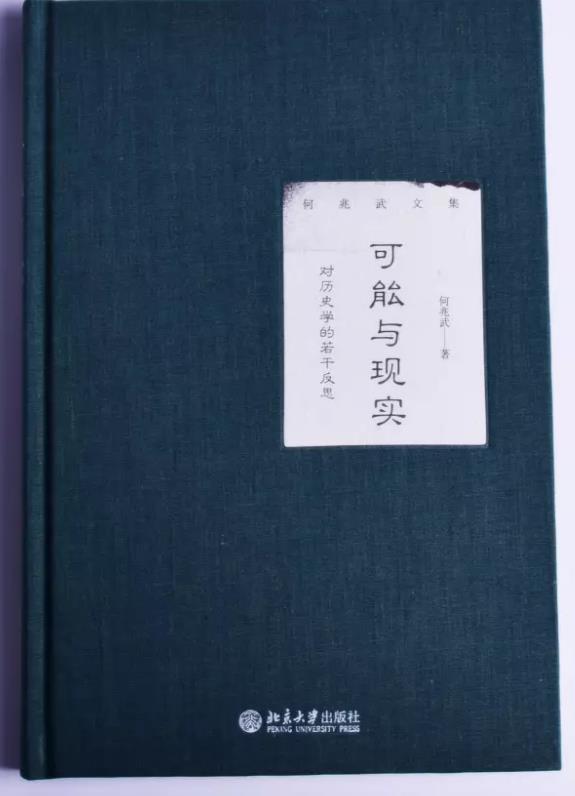
《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何兆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三、历史的两重性与历史学的两重性
访问者:您对历史学的性质有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是关于历史的两重性和历史学的两重性问题,对我们思考史学理论的根本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您的这些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或者说在您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哪些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呢?
何兆武:19世纪末西方哲学上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都流行了一阵,但是新康德主义的命运有点坎坷。第二国际提出一个口号:回到康德。可是由于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列宁搞第三国际之后批判了它,这有点儿殃及池鱼,弄得新康德主义在中国没有很好的介绍,而它对西方的影响太大了。
近代科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思想,19世纪时人们就都向科学看齐。伯里曾经说过:“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历史学成为一门实证的科学。但自然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记得我们下乡去搞“四清”,找个村干部来说:“你老实交代吧,你偷多少斤粮食?”他一看那个架势,知道不承认是不行的。好!说偷了500斤。“500斤? 老实告诉你,我们掌握你的材料,你好好交代!”他一看500斤也是不行的,涨成1000斤。“1000斤? 你回去好好想!”明天你再叫他来,他还会涨,要他说多少他就说多少。但这个土地却不听你的,亩产多少,它不会给你凑这个数。
访问者:我个人认为历史学的两重性是很难分开的,考订和解释是互相包含的。您是否认为历史学科和历史学之间是不能分开来讨论的?
何兆武:对科学的广义理解,西方在18世纪有一个思潮,那是非常有影响的理性主义思潮。但结果这个理性主义把非理性的东西都否定了。我觉得真正的理性主义应该很好地承认非理性的东西。不可能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理性的,不承认非理性的地位反而是不科学、不理性。所谓非科学、非理性并不就是反科学、反理性。
访问者:90年代时您和庞卓恒先生对历史学的性质等问题有不同看法,这些问题上您是一派代表。庞先生认为历史研究是要研究历史规律的,而历史也是存在规律的。他说过,历史研究不能探讨规律,历史学家不如回家去放毛驴。没有看到您对他的观点的回答,您是否还要和庞先生争论下去呢?
何兆武:《史学理论研究》发庞先生文章的时候就给我看了,问我是否要回答。我觉得庞先生的观点和我的没有矛盾,他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历史没有规律,而是说这个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同的。历史学如果是科学的话,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

四、西方史学的引入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访问者:我觉得您的成就不光是在史学理论方面,您翻译的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正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潮,影响广泛。为什么您会想起来去翻译这本书呢?
何兆武:我倒不是去赶时代的浪潮,因为我摸不清时代的脉搏。我是一直都对18世纪的理论感兴趣,翻译卢梭也是,后来翻了几本书都是关于法国革命的。法国革命毕竟是一件大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思想上是一回事。自由、平等、博爱都是那时候提出的。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不能光听原告的,也要听被告的。一方面我们知道那个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要知道反对革命的理论。柏克代表的是反对革命的理论,我觉得两边都需要听。
我们应该吸取百家之长。特别是一个理论可以流传几百年,必然有它值得重视的成分。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主张“破四旧”,但都砸烂了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会倒退到原始人。其实当时也没有真正彻底砸烂,民房他们砸烂了,天安门就不砸,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为什么不砸? 所以,彻底砸烂是说不通的。比如语言文字也是过去遗留的,彻底砸烂了,我们怎么活呀! 这些东西都是长期的文化积累,这你没法砸烂。
访问者:我们的课题主要是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其中也要关注西方史学近20年来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我们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您觉得西方史学对当代中国的史学有什么影响? 主要在哪些方面? 这些年您翻译了这么多的东西,对这些问题是有认识的。
何兆武:我在生活上偏食,很多东西都不吃,这没有道理,其实一个人杂食最好,人体需要吸收各种营养。杜甫的诗说得好,“转益多师是吾师”,各种营养都应该吸收一些。
过去看问题太简单,其实精华和糟粕不是截然对立的,要看你怎么看,看你怎么吸收。例如原子能,可以危害人类也可以造福人类,全看你怎么用。过去我们对糟粕、精华理解得太肤浅,太机械了。我们过去是这样的,凡是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的东西可以译,凡是马克思以后的西方的东西一律是内部发行。马克思以后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我想也有些东西是有用的。
比如说波普尔,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可我觉得他里边有些内容是有道理的,而当时我写评论时就没有写。我觉得他有一个论点值得我们考虑:他说你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如果别人认为不好的话,你就认为是他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并不是你的制度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倒过来了,究竟你优越不优越,不是大家认为你优越不优越,而是如果他不认为你优越,他就有问题,这就等于先天地承认你就非优越不可。“文革”的时候就是这样,谁不赞成,谁就是敌人,问题就颠倒了。本来是要证明我这个是最好的,现在成了谁不拥护我谁就不是好东西,结果就只能是大家“拥护”,这个“拥护”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这种思路连我们的某些领导人都有,曾经有领导人对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讲: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讲法很有问题。这个优越性不是我们论证出来的,而是要用事实来证明的,你拿出事实来我们就论证,你拿不出来我们怎么论证? 比如说全世界都吃不饱,而我们却吃得好、吃得饱,那我们可以给你论证。过去的做法等于给你事先假定了一个前提,科学或学术应该是研究的结果,不能事先有一个结论。又好比一个运动员,他要你来论证我必然跑第一、拿金牌,那你得自己去跑,不是我论证出来的。我觉得波普尔这个观点值得我们考虑。
确实是这样。过去我们能够听到、看到的东西太少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1980年,以前从来没去过。当时参观他们各个学校或者研究中心,可以看到他们的资料包括大陆的、港台的、西方的、日本的都有。可是我们在国内,要看一点台湾地区出版的资料,借的时候还要党委特批,所以我从来没借过,怕找麻烦。人家会问:你干吗借这个?
没有一种绝对唯一的方法,路数可以不同,不要简单化。反对的意见也可以听,没有道理的话更能坚定我们的信心,有道理的话就可以促使我们更提高一步。
访问者:没有唯一的道理,要靠我们去摸索。那么您摸索出来的这条道路是怎样的呢?
何兆武:我没有道路,我们是报废的一代。我也没有了解西方历史哲学。我觉得要对西方哲学了解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自然科学,可是我不懂自然科学。
过去我向单位领导建议过,进人的时候进这么几个人:搞自然科学的,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中国思想史;还有搞现代哲学的,招这两种人很重要,比如侯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史》,缺点就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思想。
原标题:何兆武│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注:此篇访谈为《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附录,有删节。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3期。访谈者: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访谈于2002年1月11日在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寓所进行,参加访谈的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邹兆辰、江湄,研究生刘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