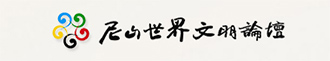林安梧 何昭旭:儒学是“活生生的存在”——林安梧先生访谈录
2025-12-10 10:01:19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 作者:林安梧 何昭旭
编者按: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2025年,“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组成员何昭旭博士对台湾学者、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林安梧先生进行了专访。林先生讲述自己对儒学的体认与理解,以及参与编辑、出版《鹅湖》月刊背后的故事。本刊特先刊出,以飨读者。
一、于生活中感受儒学的生命力
何昭旭:林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您祖籍是福建漳州的,您祖上是什么时候搬到了台湾?
林安梧:我祖先1751年从福建迁到台中,那时候应该叫彰化。我现在查了一下,台湾中部来自漳州平和的人非常多。有可能那一段时间,平和那个地方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大家都到台湾去了。为什么去台中,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漳州地形、地貌跟台湾中部几乎没什么两样,二者太像了,生活上觉得很舒服。那时候台湾人口不多,土地开垦出来就是自己的,加上环境各方面都与福建老家很像,所以很多人就会跑到台湾去。到台湾去以后,自然也把原来的汉文化传统带过来,就把这里汉化了。这个很有趣,闽南人很多习惯基本上都是中原习惯。而这些文化传统与习惯从中原南迁以后,又迁到了台湾。
何昭旭:这也说明汉文化的生命力还是挺强的。
林安梧:非常强。它有几个表现,如聚族而居、祖先崇拜、都有自己的经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民间扎根、生长,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即使在台湾被日本人占领的时代,基本上大家还是延续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是拜自己的神、拜自己的祖先。
何昭旭:您的童年也是生活在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吗?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林安梧:是的。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大,是哥哥。其实乡下都是这样,家庭成员非常多。像我的家族,成员比较多,但是我们后来建了一个新房,整个家庭搬出了原先家族聚居的那个地方。
童年生活对我后来体悟儒学思想影响很大。因为农村的家庭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组织模式,聚村而居,聚族而居,从家族、家庭所衍生出的人伦,离不开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在农村体会很深,也是自然而然的。在农村的这些人,不管是男男女女,只要按照这样的生活步调走,走着走着,到了一定年纪,这些全部都印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人们的行事也都合乎儒家的伦理规范了。我在乡下里面看到都是这样的,主要跟他们劳动的方式、整个社会的组织和构造的方式以及整个生活的形态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我对“儒学游魂说”这种观点就觉得不可思议,有什么游魂?儒学怎会是游魂?生活里面都是儒学的印记啊,我生活周遭的人都是浸润在儒学的氛围中啊。以前我小时候是如此,后来到南洋、到马来西亚一看,马来西亚也是如此。有些学者他们没有接触实际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欧美地区,当然会以为儒学成了游魂,其实儒学还活生生地存在着。中国大陆也都是这样的,儒学还是活生生的。
二、关于《鹅湖》月刊
何昭旭:《鹅湖》月刊在1975年创刊,您是这本杂志的第一代参与者,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使您参与到《鹅湖》的工作中呢?
林安梧:我常说《鹅湖》月刊的存在算是台湾的奇迹之一。台湾是有一些奇迹的,譬如《鹅湖》月刊,譬如《思与言》。因为这些都是民间创办的刊物,而到现在为止都还存在。
我进入台湾师范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鹅湖》刚创刊的时候。我当时考上大学以后,就去拜访杨德英老师和蔡仁厚老师。他们就跟我说,有一个新的刊物叫《鹅湖》,是刚创刊的,你上大学以后,可以到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问一问。我去问了以后,结果人家说没有这个刊物啊,后来才知道原来国文系本身是没有的,它是民间自己办的。我真正认识《鹅湖》,是因为张素贞老师。她介绍我去见她的学长,就是王邦雄老师。王邦雄老师当时就已经是《鹅湖》月刊非常重要的成员了,之后担任《鹅湖》月刊社的社长。
《鹅湖》月刊其实是这样的:大概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当时毕业的一些学长,就是1975年毕业的一些学长,他们跟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一些学长在1975年创刊的。这等于是他们当时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了,创办了这个刊物,而我才大学本科一年级,因为蔡仁厚老师、杨德英老师,就参与到这里面,之后很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义务地帮忙了。因为这个刊物完全属于民间的刊物,它没有什么经费,基本上都是靠着订户的微薄经费以及一些老师、学生们的捐款来维系,当然主要是老师们的捐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义务做事。
我正式参与大概是到1976年的夏天。1976年的夏天之后,我就已经成为正式的执行编辑,主要工作就是帮忙校对、出刊的时候去帮忙处理一些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参加读书会。《鹅湖》月刊当时有编辑部举办的读书会,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学长带学弟读书,并且办得非常兴盛。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读欧洲哲学家波亨斯基的《哲学讲话》。后来我们又读牟宗三先生的《现象与物自身》,当时不一定能读懂,但是慢慢地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带出来了。
《鹅湖》每一期都有非常多很好的文章,因为担任编辑要校对文章,我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开始进入到哲学的氛围里面。《鹅湖》一年十二期,几乎每个月你都会觉得过得好快,怎么一下子就过了一个月,一下子又过了一个月。当时我也发觉到《鹅湖》里面有一些朋友们的想法并不是完全跟牟先生一样,因为《鹅湖》创刊的宗旨基本上就是广义的“为中国文化而奋斗”,不仅限于牟先生这个门派,所以大家还是蛮自由的。《鹅湖》月刊之所以取“鹅湖”这个名字,就是取义朱陆的鹅湖之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学术论辩之所。
《鹅湖》月刊从我参与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家轮着帮忙做,现在我还是里面的资深编委、社务委员,以前也曾担任《鹅湖》的主编、社长。很多人大概都担任过《鹅湖》的主编,很多人也都做过社长。其实当《鹅湖》的主编或者是社长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觉得你到了这个地步,就要去担这个重大责任,是一种非常公开、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当社长、主编其实是有责任而没什么权力的。这个过程让我真正参与到一个活生生的刊物里面去,会深深感受到儒学是活着的,而且是参与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的。
那时候老一辈的先生像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在上面发过文章。曾昭旭先生当时是主编,我们是编辑。曾昭旭先生是刊物的灵魂人物,他担任了很长时间的主编,对《鹅湖》的发展非常重要。曾先生大我十多岁,他的思维很缜密,表达非常清楚,负责《鹅湖》的时候是很仔细的,我们也就跟着学习。像王邦雄、曾昭旭两位先生,虽然他们都没教过我,但是我都称为老师。
何昭旭:您觉得《鹅湖》在创刊时候的设想和思路,和它后来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林安梧:《鹅湖》月刊在1975年创刊的时候,基本上是继承着中国文化本根的一种发展思路。当时唐君毅先生有一个说法大概就是“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然后就是再寻求“灵根自植”。而既然要“灵根自植”,它在各个地方都要“灵根自植”。在台湾,《鹅湖》月刊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灵根自植”,而参与者主要是香港的一些朋友与台湾的一些朋友。所以,大概可以说《鹅湖》后来就慢慢成为港台新儒家的一个“机关刊物”。与此密切相关而受学于牟宗三先生的学者,被称为“鹅湖学派”。像河北大学著名教授程志华就著有《台湾“鹅湖学派”研究——牟宗三弟子的哲学思想》一书。
三、对儒学的澄清与诠释
何昭旭: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成为现实,而不再只是愿景,这个时候对中国的主体文化很有必要进行重新回顾与定位。因为现在很多人对于儒家、儒学不了解、有误解,甚至是有完全错误的认知——他们头脑中的儒家,恰恰是儒家所反对的东西,比如说迂腐、懦弱、保守,比如“官本位”思想。为什么今天一提儒家,它好像就成了权力的附庸了?
林安梧:儒家主张民本,不是官本。儒家好像成了权力的附庸,这就牵扯整个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按照我的理解,用“类型学”区分的话,儒学可分为三个类型:你刚才所说的,也就是公众常提的,叫“帝制式的儒学”,围绕君主专制逻辑展开的;其二是百姓民间的,叫作“生活化的儒学”;另外一个就是士大夫儒学,它具有批判性,也可以叫作“批判性的儒学”。帝制式的儒学、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这三个我们可通过一个概念类型来区分,就是在“理”上可以作出区分,但是在现实中它并不是有某个部分就只是那个部分,它只是以那边为重的。譬如说帝制式的儒学里面,它跟生活化的儒学有没有交涉,跟批判性儒学有没有交涉?其实也都会有交涉的。但是我们要区分一下,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批判性的儒学角度来讲,意思是:你做国君要像个国君的样子,做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做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但是从帝制式的儒学角度,就理解成君做主导,臣要在君底下,所以“君为臣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原先也不是那么强制的关系,它的意思就是既然君为臣纲,所以你君要做好,发挥主导作用;父为子纲,所以父要做好;夫为妇纲,所以夫要做好。后来慢慢地就变成:君为臣纲,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夫为妇纲,所以为人妇的,一定要服从夫,甚至夫死也不能改嫁。其实改嫁在中国历代都是非常平常的事,而且法律上对改嫁都有明文规定,比如说丈夫过世,你改嫁的时候,你的财产能带走哪些,宋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
现在我们不再提“三纲”,而经常提“五伦”。“五伦”是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它基本上变成我们所说的大约是一种接近于对等的关系,而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
何昭旭: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现在的工作,就是要重新揭示这些被遮蔽的儒学概念,去伪存真、正本清源?
林安梧:大致可以这么说。我目前关切的事情是经典怎么诠释,它跟我们生活的关联是什么,经典的诠释放到当代的文明互鉴下能发挥什么作用,与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学术怎样交流对话。比如说“天地君亲师”怎么诠释,比如说“孝悌慈”这三个字怎么诠释。“孝悌慈”是整个中华文明永生的奥秘,何以这样说呢?“孝”是我们对生命根源的纵贯的追溯和崇敬。“悌”是什么?悌是顺着生命根源而来,横面的展开跟连接。“慈”是什么?慈是顺着生命根源的纵贯的延伸。你看我在作诠释的时候,其实就有意地把它们跟现代的学术结合在一块去理解的。
何昭旭:现在公众对儒家学说还有一个误解,认为儒家学说是贵族的学说,或者说是服务于贵族的,这可能还是受阶级叙事观点的影响。
林安梧:儒家学说怎么是服务于贵族呢?文化教育原先是贵族的教化没错,贵族是劳心者,民众就是劳力者,孔夫子之前一直这样的嘛。中华文明发展到春秋时期,孔夫子开启了平民教育,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贵族”。原来是贵族才有文化,平民没有文化,此后就不是了。所以“君子”这个概念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社会阶层的概念,而是变成了一个德性的位阶概念。你只要读书识字、有觉性,就能够自己成就自己。生命有一个自我修为的发展过程,所有人都能成为君子。
人的地位是有高低的,修为是有品级的,以前地位高就代表修为高,自孔夫子的时代开始转变了,地位与修为开始分离,修为品级优先于职务之高低。这很了不起啊。孔夫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强调修为品级优先于地位高低。像陶渊明,他当一个小令,在社会阶层上并不高,但他的诗词、自由精神、隐士思想,成就了他的君子人格,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表征,所以他被历史记录。这就是修为品级优先于地位高低,这个评判标准是被我们中国人共同体认的。所以,生命要有一个本真性,要有一个自然性,回归到生命本怀,回归到整个天地之间。要回到那里去,这样才能够成就一个最真实的自然之人。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复苏的可能,文化也必须是这样的。
陶渊明了不起,他比较接近道家,但也隐含儒家的思想,由此我就想起台湾雾峰林家那一副对联:“自题五柳先生传,任指孤山处士家。”五柳先生当然是指陶渊明,孤山处士是指梅妻鹤子的林逋,二人都是隐士。这副对联彰显着雾峰林家的精神:即使是在日本的统治下,这里还是我中国人的文化区,我隐居在这里,一代一代传承自己的文化。字句就在那个地方,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懂,但是我们讲一讲就懂了,对民间的这些传统就理解了。讲解之下就呈现出一种思古之幽情,这种情怀是我们华夏文明最可贵的地方。
何昭旭:我感觉“中庸”对中国人的精神塑造很关键。中国人好像擅长中庸,不过可惜,近代以来,中庸被污名化了。
林安梧:中庸它有多重意涵。中庸是以中道为体,以和为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什么?就是宇宙造化最内在的“根荄”,那就是一个至善之源。中庸落在民间,它变成不要过分,“和”变成和稀泥的和,逐渐地变成不好的东西,成了“差不多先生”,但这不是中庸本来的意思。现在我们传承儒学,就要好好地回溯本源。
民国以来学者对儒学的污名化,完全是搞错了对象,该批判的对象不是儒家。他们是因为没有能力去面对君主专制,没有能力去面对父权高压,没有能力去面对男性中心、男权中心,最后拿孔夫子出气。这是不对的。其实需要批评的是,是什么造成了孔子的思想变成了那个样子。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孔子与阿Q》来探讨这个问题,孔子是一个道德理想形象,阿Q是鲁迅笔下的中国国民性形象,那何以至此?你不能说鲁迅笔下的阿Q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原来的理想人格是孔子的形象、是老子的形象,为什么到最后变成阿Q了,要去探讨这个问题。一个很高的理想人格,要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后来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就转向内在,变成境界的修养,境界的修养也达不到,变成精神胜利,最后变成阿Q。所以很多这种问题需要去厘清,光批评是无用的,批评也要有真正深入的批评。
作者简介:
林安梧,中国台湾人。现任山东大学易学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院长。曾任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何昭旭,历史学博士,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编辑:张晓芮】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