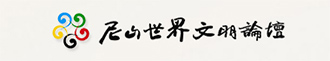沈顺福:义即准则
2025-12-22 15:05:23 来源:《孔子研究》 作者:沈顺福
义是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不仅构成了儒家人道论体系,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影响至今,如现代汉语中常常出现讲义气、正义等表达。那么,在传统儒家那里,义具有哪些内涵呢?以往的学术界对义的内涵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如唐君毅说“由义之古宜,皆自客观之事之宜上言”、劳思光先生将义解读为“道理”、以及有学者将义利关系理解为“义务和权利的关系”等等。本文指出:在儒家哲学体系中,义是作为普遍而客观法则的仁的具体形态与主观(主体)形态。这种作用于心灵的、能够决定某个具体行为性质的法则便是现代伦理学所说的准则,义是准则。
一、义是客观之道
作为传统儒家核心概念之一的义,其基本内涵是适宜。孔子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用义的方式去使用百姓是君子之道,其中的义便指某种正确行为的性质。反过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义乃是某类行为的性质,不义便是没有此类性质的行为。孟子也用义来指称某类行为的性质,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公孙丑上》)义即指某类行为的性质。“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离娄上》)君子做到仁与义,天下人便会随之而为,义是某类事情或事迹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义被抽象化为一个概念,指称某种抽象存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其中的义是一个抽象概念,指称某种适宜性。适应性简称宜。《礼记》明确指出:“义者,宜此者也。” (《礼记·祭义》)义即宜,表示行为的适宜性或合理性。扬雄曰:“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义即适宜。程子曰:“义,宜也。”义即宜。朱熹曰:“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矣。”义是作为正确行为方式(“路”)的行为的性质,义即适宜性。
适宜之义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双重品格。当义被用来指称某种客观性活动的性质时,这种性质同样具有客观性。孔子曰:“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卫子》)君臣之义指某种能够协调人际关系的法则,具有客观性。故,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论语·学而》)信可以被理解为客观陈述,义则指客观之道,合起来说,信接近于本真存在即客观法则。这里的义主要指客观存在。事实上,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论语·卫灵公》)义是主体内在部分,这种内在部分义既可以是主观之道,也可以被理解为作为主体部分的客观实在。
孟子将心视为义的源头,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义产生于羞恶之心,是心的活动或反应,或曰“内心的正义感”。义出自于四端之心。同时,作为反应主体的心是人的自然禀赋,人们通常将此类禀赋叫做性。故,四端之心即性。仁义之本源便可以解释为性,即,仁义出自于性。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义等出自于人的自然之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仁义出自于本性或四种心。如果说人的自然禀赋之性是客观存在,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义便也具有某种客观实在性。
荀子将礼义视为道,曰:“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荀子·儒效》)义是公道即公共法则,也是正确行为的标准。义之所以成为法则或道,原因在于其本来属于某种客观行为的性质。一旦将这种性质概念化或实体化,它便转换为某类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方式。“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 (《荀子·天论》)和其他自然存在相比,人的特殊之处在于礼义,即,礼义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具有客观性。这些法则作用于人心:“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 (《荀子·强国》)这些作用于人心并因此能够节制人的情感等活动的义具有客观实在性,即,只有某种实体存在才能节制人心的活动。“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作为法则的、实体之义能够作用于人心。“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 (《荀子·王霸》)义通过作用于心,影响到人的志、意以及身体活动。“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荀子·礼论》)礼义能够养欲、养情,其中的欲或情都是心所发动的活动,义便通过作用于心而影响到人的情、欲等行为。
《礼记》接受了荀子的立场,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礼记·礼运》)十种人义乃是十种人类行为原理,是公道。在人人求私利的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礼记·礼运》)只有作为公共原则的义才能保障群体的秩序。这些抽象的公共规则最终必须落实于具体行为之上。《礼记》曰:“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 (《礼记·礼运》)仁是众多的公共存在,义则是针对于某个具体行为的具体法则,依据此法则产生的行为便是义。《礼记》曰:“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 (《礼记·祭义》)仁是公道,义是适宜的法则即准则,礼是举止。这种具体法则能够对主体之心产生约束:“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礼记·乐记》)义即能够规范自己的法则,具有实体性。“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 (《礼记·丧服四制》)能够规范主体的机制便是理,也叫义。义是适宜的客观法则。
董仲舒明确提出:“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圣人见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应万,类之治也。”义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行为原理,是人道。“天志仁,其道也义。”天道好仁,其道便是义,义也属于天道。比如,“官职之事,五行之义也。”职官的行为原理源自于五行原理,其中的五行原理即义便是自然原理,属于天道。按照天人相类的原理,人效仿天,人道也效法天道,即,人道之义源自于天道之义。作为天道的义存在于自然界,具有客观性。“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是天的祖孙,一切效仿天,其中的天理即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义。此时的义乃是某种客观的人类行为法则,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具有客观性。“《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义也,真其情也,乃以为名。”名乃是对真、义、情的描述,其中的义便指某种客观存在,名则是对此客观实体的如实再现,这种客观实体便是客观之道。义是某种客观实在。这种客观性作用于心,能够对心产生某种约束即“节”。这种节,从康德道德哲学来看,是约束(obligation),并因此能够规范人心所主导的行为。但是它区别于具有个体主体性的“义务”(duty)。将义等同于义务并不准确。
二、义是主体观念
作为客观行为的性质的义,产生于人们的认识,即,适宜性乃是人们对于某类行为的性质的认识。因此,适宜性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并由此构成了义的主观性。准确地说,义出现于人的心灵状态中,从而获得了主观性。孔子曰:“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论语·宪问》)乐、义是人的感觉或判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 “闻义”之“义”应该指某种可以被认识的观念或规则,具有主观性或经验性。“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卫子》)君臣之义即君臣之间的交往规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敬畏鬼神而远之便是众人对待神灵的原理。这种作为原理的道可以被理解为某种观念,义是观念。
孟子将义视为心的自然反应。孟子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 (《孟子·告子上》)义产生于人先天禀赋、内在于天生之心。适宜完全出自于人的自然反应。这便是“义内”说:“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 (《孟子·告子上》)义是一种基于人的自然之心而所产生的某种自然的感觉或反应,并因此天然地具备某种主体性或主观性。这种反应乃是心对于道的认可,义等同于道。孟子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心自然好理、自然生义,这里的义等同于道。义即对道的接受。
当主体之心接受了某种道并产生某种感觉或判断之后,主体可能会将这种感觉或判断对象化、从而转换为某种主观观念。这种观念便是规则。告子主张仁内义外:“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告子上》)义是一种外在的经验规则。比如,“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孟子·告子上》)对他人的尊重之义并非出自于我的本心,而是某种人为规定。义被告子视为某种人为规则。
这启发了荀子。荀子直接从认识角度讨论了义的内涵,以为义是“通义”(《荀子·仲尼》)。“通义”即普遍的规则或观念,比如,“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 (《荀子·非十二子》)义即规则,如君臣之义便是臣子面君主时的行为原理或规则等。义是某种规则或观念。“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荀子·劝学》)学习的对象是经典,经典的内容便是各种规则或观念即义。如《礼》便记载了各种规则(“纲纪”),这些规则便是义。 “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 (《荀子·劝学》)只有将所学的仁义观念落实于所有的行为中,才是真正的善学。“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荀子·不苟》)这种仁义规则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思想,最终能够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中。这种落实于具体行为中的规则便是准则。这些规则或准则乃是圣人制作:“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荀子·荣辱》)义乃是由圣人制作的、主体接受的规则。这种接受表现为适宜。适宜体现了主体对某种规则的认可与接受、从而成为某种行为的准则。“礼义教化,是齐之也。” (《荀子·议兵》)这些规则的目的便是为了教化。“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荀子·荣辱》)按照这些规则,行为者能够举止合乎规定,最终形成一个和谐共同体。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仁与义的关系。董仲舒曰:“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道能够提供万物之生命,故而为施。与之相对应的人道在于义。义是人类行为的法则即人道。“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 作为人类行为原理的义乃是对天道的效仿,即,人道参照天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人类法则的义取自于阴阳之天道。这种效仿关系暗含了义与仁的关系,即,作为人类行为法则的义乃是天道之仁的具体化。
同时,义不仅出自于仁,而且还是仁道的主观化,即,它是作用于人心的道。董仲舒曰:“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义是主体的某种感觉或认识。“辞已喻矣,故曰: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託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圣人制作的义表达了尊卑贵贱的观念。义是一种经验规则。“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义出自于经典,也是圣人宣讲的内容。这种能够被宣讲的法则便是规则。它能够进入人们的心灵并因此影响到人心的活动。“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义的目的是规范(“正”)行为主体(“我”)。这种规范发生于心中并能带来心“安”:“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 (《荀子·强国》)义能够带来心安。心安是一种主体体验或认识,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观念或经验性规则乃是普遍之道的主体化或主观化。
三、义是用
义乃是心对于作为法则的道的接受。这种接受,在理学这里表现为体用关系,其中,仁或道是体,义是用。程子曰:“言义又言道,道、体也,义、用也,就事上便言义。”道是体,义是用。作为用的义包含了体,此体即道、理或仁。程子曰:“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语道矣。”仁即道,为体,义是其发用。这一发用并非说是仁即性体的独立活动,而是说性或理在心中而呈现出来的活动。活动即用。“道无体,而义有方。”道是无形体的实体,义则是具体应用。“既生得此气,语其体则与道合,语其用则莫不是义。”道或理是体,义是发用或应用。朱熹曰:“仁固为体,义固为用。然仁义各有体用,各有动静,自详细验之。”仁即天道,在人便是性,属于体,义便是其发用。“仁义互为体用、动静。仁之体本静,而其用则流行不穷;义之用本动,而其体则各止其所。”仁是体,义便是其用。用即作用或行为。“敬便竖起,怠便放倒。以理从事,是义;不以理从事,便是欲。这处敬与义,是个体、用,亦犹《坤卦》说敬、义。”依据于理而作为便是义,其中的理是体,义便是其发用。 “敬、义只是一事。如两脚立定是敬,才行是义;合目是敬,开眼见物便是义。”敬是敬仁体,其展开之用便是义。义是活动。“须是彻上彻下,表里洞彻。如居仁,便自能由义;由义,便是居仁。”仁是体、义为用,居仁之体必然产生义之用。“不可执定,随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义。”义即依据于理的活动。王阳明曰:“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义即是适宜,乃是心的活动。“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在“义极义”中,前面的义作动词,后面的义表示义理,义即穷尽义理。这种穷尽义理的活动便是义。义是心的活动。活动即用。义是用。
作为用的义具有两项内涵。第一项内涵是主观性,即,义是主体之心的活动,从而具备了主观性或主体性。程子曰:“理义,体用也。理义之说我心。”理在心中便是义。义是心的活动。“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之气睟然达于外。”仁义出自于仁义之心。“不动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义在心中、制约着心的活动。故,义在我,是“我”的活动。“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仁义在心中。心中之性便是义的终极依据。这种依据之仁是体,义便是其活动。 “义之在心,乃是决裂果断者也。”义是心的活动,准确地说,义是性在心中所产生的活动。“如适来说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发而为恻隐,这便是仁;发而为羞恶,这便是义;发而为辞逊、是非、便是礼、智。” 这种心中含性的活动便是恻隐、羞恶、辞让等行为,其中的羞恶便是一种具有义的性质的、由心所主导的活动。王阳明曰:“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谓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义是心的感受或活动,义是当然或应然,其依据则是心中的良知。“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义最终源自于心,属于心的活动,其主体是心,其依据是良知。王夫之曰:“性者天道,心者人道,天道隐而人道显;显,故充恻隐之心而仁尽,推羞恶之心而义尽。”在心的作用下,天道最终落实为具体的羞恶之事。这种羞恶之事所遵循的原理便是义。当我们说义是心的活动时,义便属于客观之道的主观化或主体化形式。
义的第二项内涵是具体性,即,义是具体事上之理。二程曰:“只有一个义理,义之与比。”理是形而上之体,最终落实于具体之事上便是义。义是事中之理。“圣人缘人情以制礼,事则以义制之。”作为公道的义的功能便是约束心,最终形成某种规范性行为。“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义的功能是用某种公共之道来规范私心、表现于具体事之上。
朱熹甚至分别了理的种类,提出理一分殊说。朱熹曰:“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着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着义,便有礼智相对。……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在理一分殊关系中,仁不仅是普遍之理,而且还是特殊之理。“天理既浑然,然既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却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天理既是一,又是多,即,仁之下又分别出仁义礼智四种理,其中,四德在天理之中,如同种属关系,即,四德是种,天理是属。这便是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具体于具体事上的理乃是天道之属下面的一种理。正是这种理决定了事的适宜性。朱熹曰:“义是其间物来能应,事至能断者是。”义是某个特殊之事所遵循的理。义是事。“涵养须用敬,处事须是集义。”遇到事情之时符合道理便是义。朱熹曰:“天下莫强于理义。当然是义,总名是道。以道义为主,有此浩然之气去助他,方勇敢果决以进。如这一事合当恁地做,是义也。”道是总名或一般原理,落实在此便是义(“当然”),即,义是道的某种具体形态。两者可以合起来,“道义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若道义别而言,则道是体,义是用。体是举他体统而言,义是就此一事所处而言。如父当慈,子当孝,君当仁,臣当敬,此义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则道也。”道是公共原理,义是当下使用中的道,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义是在某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公共原理,从根本上来说,义也是道,只是义是具体之道。王阳明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义即良知,作用于具体之事上。义即事上的良知。“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集义便是致良知、便是具体去做,义即具体事上的良知或理。王夫之曰:“道是志上事,义是气上事。”当公共规则具体到事上时,便转化为具体行为的法则。义即具体事上之理。
四、准则与行为
义在心中,体现了义的主观性;义在事中,体现了义的具体性。故,从这个角度来看,义是普遍而客观之道的主观化与具体化形态。假如我们承认仁道是某种普遍而客观的法则,那么,义便是这种普遍而客观的法则的主观化与具体化形态。其中,主观化表现为义在心中、具体化表现在义在事上。这种主观化与具体化形态的法则,从人类实践的角度来看,便是准则(maxim)。
康德说:“准则是行为的一种主观原理,必须与客观原理即实践法则区别开来。前者包含了理性依据于主体条件(通常指其无知或偏好)所设定的实践规则,这样,这一原理便决定了主体的行为。但是法则是客观原理,对于所有的理性存在来说都有效,依据于其而行动的原理便是命令。”作为行为原理的准则包含两个特征,其一,准则是主观的,即,准则乃是作用于人类心灵或意志的行为原理,能够对主体的行为产生主导作用,准则即心中的法则。其二,准则是特殊的,即,准则乃是某个具体行为或活动的行为法则,具有具体性或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作为目的的质料。康德说:“质料即目的。这里的公式是说理性存在者,不仅以本身的本性为目的、因此以自身为目的,而且必须在所有的准则中设置条件来限制那些相对的、任意的目的。”准则包含了某些质料。这些质料成为的欲求的对象并因此而成为目的,其中蕴含着主体选择与偏好,存在着“建立在欲望与偏好基础之上的准则”。比如人类的自爱便可以作为质料而被追求、并因此而成为准则的内容。不过,这些单纯的、由质料所形成的、能够确定行为目标的主观准则并不可靠。为此,康德认为,准则还应包含某些普遍性形式:准则的“形式由普遍性组成,从这点来看,道德命令的形式如此表达,即,准则必须如此选择,好像它们能够被当作自然的普遍法则来使用。”客观法则的形式成为准则内容。准则是客观法则的主体化。康德说:“当我剔除了意志中的由其他法则而产生的冲动因素时,便只剩下其行为与法则的普遍一致性,它自身便能够成为意志的基础,即,除非我能够让我的准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否则我绝不去做。此时在这里,只有与法则的一致性,而不考虑任何的适应于特定行为的特定法则。”这些法则(的形式)成为某种合法行为的准则的客观基础。法则形式所具备的必然性为准则提供了必然性:“当我们设定一个定言命令时,我立即明白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它只有如下一般陈述,即,行动的准则必须与普遍法则保持一致。正是这种一致命令才能具有必然性。”来源于客观法则的形式的准则因此获得了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成为准则作用于人类心灵的定海神针:“设想只有准则的立法形式自己成为意志的决定性基础。”准则因为有了这些客观必然性而成为意志的决定者,必然地决定了意志活动的性质。这种决定意志的必然性便是义务。康德说:“义务和约束是我们称呼我们和道德律的关系仅有的名称。的确,我们不仅以自由的身份而可能成为(由理性呈现于我们面前而成为尊重对象的)道德王国里的立法成员,而且我们在其中,不是主宰者,而是臣民。”普遍性法则如理对个体心灵的约束而产生的关系便是义务。通过这种约束,个体得到心灵受到了规范,而且能够因此将个体性行为规范化。义务确保了“行为的必然性,也叫实践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作用于心灵,便是一种约束或“制裁”。通过义务关系,人类主体得到规范。康德说:“依据于原理的行动即义务的实践必然性并非立足于情感、冲动或偏好等,而是仅仅依赖于理性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理性者的意志必须总是被视为立法者,因为除此之外,它便无法以自身为目的。这样,理性将自己视为普遍的立法者,将其意志的全部准则提供给其他的意志和其他人的全部行为,让它们以我为准.”义务能够规范人的情感与私意,让心灵或意志具备了合“理”性。合理性之理便内在于准则之中。这种在某种准则指导下而产生的行为因此能够形成一个秩序的整体或群体。
准则是客观法则的主体化与具体化形态。这种关系同样体现在理学视域中的仁义关系论中,其中,仁是天道,是所有法则的集合或属,而义便是人道,决定某个具体行为的法则。仁义关系不仅是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关系,而且还是客观与主观(主体)的关系,即,义乃是普遍而客观之仁(道)在具体心灵上的形态、并因此而决定了某件事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普遍的客观法则的具体化与主体化,客观法则进入人们的主体心灵,不仅转变为某个法则,而且通过作用于人心来决定某件事的性。荀子曰:“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荀子·不苟》)君子知道通过敬畏某种来源于客观法则的主体规范来节制自己。义即约束性规范,其功能是约束人,即,“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义能够节制人的行为。董仲舒明确强调:“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义是对行为者自身的规范、义即正我。这将义与道区别开来,即,义仅仅指那些作用于人心的、具体的道,或者说,当道落实到某件事上时,道变成了义。在此时此事上约束人心的道便是义。这种义,作用于心灵或意志的具体的准则,义即准则。
当客观法则转换为主观准则时,主体便产生了“宜”的感觉或意识。这种适宜性判断便是“当”。程子曰:“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义确定了某种某种行为的正当性。“何必然?义当来则来,当往则往尔。”适当的依据便是义,或者说,只有义才是某个具体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当为或不当为的依据便是义。朱熹曰:“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义即天理的当然作用。或者说,义是天理在某件具体事上的应用。合乎义者便是适当的。“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义即具体事中的理,此事因其而正当。“‘精义’二字,闻诸长者,所谓义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处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谓义也。”义即适宜,是对事情是否合适的界定,合义便可、反之则不可。“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合理的行为便是当然之人事,比如择善、固执等行为便是某种符合理的人事、正当的行为。王阳明曰:“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义便是心中的良知的具体形式、确保了行为的适宜性即“当”。当即应该:“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应该具备了绝对命令的效力,并因此能够约束人心。“义即当然,亦即行为的制裁。”道通过制裁心而规范了人的行为。通过这种规范,人的自然活动也因此而转换为符合“道”“德”的行为,人也从自然人转变为道德人,从而获得了生存的超越。
五、贡献与局限
从现代哲学来看,儒家之义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准则。这个准则,一方面来源于普遍之道,即全部行为原理即道的具体形态,普遍之道是属,作为法则的义便是其种,二者之间形成了普遍与特殊(具体)的辩证关系。从儒家哲学体系来看,这个公共之道便是仁,义便是公道之仁的某个具体法则,仁是属,义是种。另一方面,公共仁道,在儒家看来,具有客观性,它是客观世界万物遵循的必然法则,具有绝对必然性和客观性。当这种客观法则落实于人心之中时,便演化为某个能够指导人们具体行为的法则,这种主观性法则便是准则。准则不仅能够指导某件事,而且是客观法则的主观(主体)形态,是心中之道。这种心中之道,具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体之性,通过影响人心,最终产生合“理”的行为。这便是儒家的义论。这种义论至少有两点理论贡献。
其一,将义视为公道。作为公共法则或规则的道或理能够协调而形成一个和谐的秩序的整体,如人道便是人类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作为法则的义能够形成一个秩序的整体。在这个秩序整体中,成员之间相亲相爱,互惠互利,从而产生最大的效益。这便是道义法则的功能或意义,即,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客观法则的约束、按照法则去行为,目的在于舍小而求大,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便是儒家的义利之辨。为了确保最大利益,儒家愿意用普遍法则来约束自己的心灵。这种普遍法则是道,约束心灵时的法则便是义。人们接受和遵循道、义、理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利。这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自然性原则和公共性原则,即,人们为了某种人类的自然性需求,必须遵循某些公共性规则,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普遍性原则的遵循是利益最大的最佳途径。
其次,儒家以公共之道或天理所具有的实体性确保了人心活动的实在性,避免了康德义务论中道德义务必然性的来源问题。在康德看你来,能够约束人的意志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则,但是康德似乎没有提到法则的实在性问题。事实上,康德所说的法则都是人为指定的、经验的法则,具有主观性。康德说:“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道德必然性是主观的,即,它是一种要求,而不是客观的义务。义务不会去假设某个东西的存在。”在康德这里,能够对我们的心灵产生某种影响的法则是经验性的法则,缺乏客观实在性。这便带来一个理论问题:主观性法则其必然性也是主观的,如何能够形成客观必然性呢?或者说,康德无法保证义务的客观必然性。故,冯友兰说:“儒家说无条件地应该,有似乎西洋哲学史中底康德。但康德只说到义,没有说到仁。”假如我们将仁理解为客观法则,那么,这一理解不无道理。康德法则乃至法则的形式,终究还是某种主体产物,缺乏实体性。儒家哲学将道或理视为某种绝对的、客观的、普遍的、永恒的实体。理的普遍性表明:它无所不在,所有的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理;理的永恒性表明:它无时不在,任何事物在任何时间都离不开理。因此,理是万物生存、人类行为必不可少的依据。这种依据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实体的,即,它是某种实体存在,因此能够对同样是实体的心灵产生实体性的影响。通过二者的结合,气质之心吸收了超越之理,宛如野马找到了骑手,盲目的奔驰转变为有方向的、正确地行为。这便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贡献,即,通过假设存在着某种超越而实体的法则,为普遍规则提供了存在论的辩护。理学的存在论辩护具有实在性,区别于西方存在论辩护的纯粹思辨性。
从普遍的客观法则向某个具体准则的转向,其间存在着一个难题:何种法则或规则能够成为这一具体行为的准则呢?康德选择了自主选择的机制。康德说:“在每一个行动中,意志是自己的法则。即:遵循人们都愿意将其当作普遍法则的对象的准则而行动。这便是绝对命令的公式,也是道德的原理。因此,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律的意志是同一个。”只有自主个体的自由意志才能将普遍法则转变为具体行为的准则,让道变成义。此时的义不仅遵循了普遍法则,而且也是个体自主选择的产物。在这个经过自主选择的行为中,个体不仅能够遵循普遍法则的规范、产生合乎群体秩序的行为,而且个体在此行为中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意志,成为一个自由人。在康德体系中,作为准则的来源的法则是多重,准则的产生立足于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准则来源于众多法则的选择。
儒家采用了一种辩证方式,即,将仁与义的关系理解普遍存在与特殊(具体)存在的关系,其中,普遍之仁是属,具体之义是种,仁义关系变成了属种性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虽然准确地揭示了存在的辩证性,但是,这终究属于一种认识领域的关系。准确地说,它是作为存在本身的辩证关系的对象化,因此是静态的、“死”的关系。在这种“死”的关系中,普遍存在与具体存在都被确定了,即,某种普遍存在呈现为某个特定的具体存在。事实上,与普遍存在相应的具体存在,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是众多的,即,不仅可能是此,而且可能是彼。选择此而非彼,便是意志的使命。由于儒家哲学忽略了意志内涵,从而遗忘了主体的自主性,转而选择了另一种机制,即,机械地安排或服从。在这种机制中,此、彼的确定是由某个代表整体秩序的个体来规定。群体如同一台机器或一个生命体,成员便是机器的零件或生命体的枝节。对于这个整体来看,群体的秩序是其存在的终极关怀。在这种机制之下,个体通常被忽略,转而成为整体中的被动的、机械的分子,成为可以被牺牲的工具。这便是传统儒家义论面临的问题之一。
【编辑:董丽娜】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