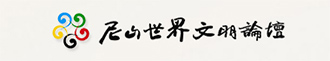东方朔:荀子的欲望概念与动机转化
从柯蒂斯·哈根的一篇文章说起
2026-01-09 10:02:21 来源:《孔子研究》 作者:东方朔
在许多学者眼中,《荀子》文本所预设的性恶之人如何会生出行善的动机这一问题,就像一个摇曳的钟摆,让人好奇,也让人着迷。荀子一方面说“人之性恶”,故“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下引《荀子》只注篇名),“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儒效》)。问题是,一个本性上倾向于自利的人如何转化为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人?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通常的思路是对荀子“欲望”概念加以深入的解释。因为按照休谟的理论,一个人行动的动机或动力总是与一个人的激情或欲望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在荀子的思想中,欲望本身若不加节制的话会倾向于犯分乱理,如是,如何转化欲望似乎构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关于此,学者基于荀子的文本,从方法、含义上给出了各种可能的解释,在这些尝试中,柯蒂斯·哈根(Kurtis Hagen,后文称哈根)的《荀子与审慎之道:作为成善动机的欲望》一文对荀子的欲望概念和动机转化问题提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解释,值得我们对此作出分析。
一
哈根的文章较长,除“导言”与“结语”外,分七个部分讨论了相关的问题。哈根首先检讨了学界对荀子动机理论的相关研究,讨论了荀子的“欲望”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对荀子“化性”观念的理解,分析了荀子思想中所包含的认可“道”的审慎态度以及对“养欲”“好荣誉”等观念的理解。但从总体上看,此文最引人注目的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荀子欲望概念的分析,二是对荀子“化性”主张的理解。哈根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荀子最著名的口号是“人之性恶”,它意味着我们天生的情性是恶的,然而,荀子并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人们能够成善。性恶之人如何成善?荀子认为,我们需要“伪”,亦即人的智识的构成物能够帮助人重塑品质。荀子相信通过努力地运用我们的心智,而非盲目地顺从我们天生的感性倾向,人们就能够发展、保持与“道”的一致并获得和谐;尽管我们的原初欲望(original desire)无法改变,但当这些原初欲望与理智结合在一起时(只要我们运用它),就可以通过增加新的动机层次来激发我们改变品性。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成德的手段在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所谓的“性”,依照徐复观的说法,基本上可以以“欲”来理解。如是,“化性”亦可表达为“化欲”,也因此,通常认为荀子提供了一种转化欲望的方法。然而,Hagen明确指出,严格地说,荀子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种方法。荀子所谓的因教化而有的动机转化并不是要求我们去转化原初欲望,而是要将原初欲望与理智相结合,通过人们有意识的训练,如师法、诵经、读礼等方式,发展出一种新的辅助性动机结构(auxiliary motivational structure)来改变我们的品性。为此,Hagen在文章中首先检讨了万百安(Van Norden)、黄百锐(David B. Wong)以及克莱恩(T. C. Kline Ⅲ)对荀子动机论的相关研究,并指出了黄百锐对万百安的不同意见。依哈根所论,克莱恩在万百安和黄百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方面,这主要表现在克莱恩对荀子“心之所可”作为一种新的动机的分析上。在克莱恩看来,荀子所谓的“心之所可”与知相连,与描述和评价我们的内在动机、外在情境的认知能力相连,如是,“心之所可”应当被理解为不同于欲望的新的动机机制。这种经由心之指向和控制的过程,将原初欲望转化成比与生俱来的随情感状态而有的直觉反应更为复杂的动机,可以体现在更为广泛的认知描述和评价之中,同时也建基于对外在因素之性质的理解和敏锐感知之中。正是基于此,克莱恩认为,荀子的“心之所可”作为一种新的动机并没有与(原初)欲望绝然分离,同时假如我们将这种已经转化了的动机依然看作是欲望的话,也会与荀子将欲望理解为天生的情感状态的定义相违背。从哈根对克莱恩的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到,哈根特别重视克莱恩的这一观点。按哈根之意,所谓荀子为我们提供了欲望转化的方法,其实只是荀子为我们发展出了一套作为辅助性动机的新的欲望,这种新欲望由于出于礼乐的教化和理智的引导而具有新的获得性的“准道德”的意味;当这种新欲望与原初欲望发生冲突时,新的欲望能够克服我们的原初欲望;当一个人成功地转化其所有的品质后,原初欲望依然保留,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如是,即可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甚至在还没有形成高尚的意图之前就有动机去遵循“道”,因为在荀子看来,遵循“道”提供了满足人的原初欲望的最佳机会,同时也提供了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更崇高的志向的机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哈根把荀子的欲望理解成两种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其一是“基本欲望”(basic desire)或“原初欲望”(original desire),这种欲望指的是人生而具有的“不可学、不可事”的欲望能力,这种欲望能力不涉及欲望的具体对象;其二是“具体欲望”,亦即对具体事物的欲望(desire for a specific thing),如“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等。依哈根所论,基本欲望与具体欲望的关系是:基本欲望是具体欲望的基础,具体欲望包含基本欲望;基本欲望根源于天,不学而成,且不会改变,而具体欲望则以经验和推理为中介。在荀子那里,基本欲望由于与可恶的性和情相连,而且也常常与感官相关,所以会有些负面的含义,但当导之以智时,这种欲望并不坏。荀子之所以说“人之性恶”,是由于欲望的特点如好利恶害、不知满足等,如果缺乏理智的引导会产生偏险悖乱的结果,但欲望本身是中性的,故而拥有欲望本身虽不值得称赞,但也不可耻。审如是,在实现欲望的道德转化时,荀子并不主张改变我们的基本的自然欲望——这种欲望不能也不需要改变,但我们必须修改(revamp)我们的动机结构,以使新动机和新欲望成为激发人们合于“道”的行动动力。
然而,问题在于,哈根既然认为道德转化并不要求改变我们的基本欲望,而这种基本欲望又表现为我们的自然情性,那么,作为荀子思想核心之一的“化性起伪”中的“化性”又该做如何理解?对此,哈根对以往学者的两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提出了批评。
一种观点认为,“化性”即是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性取代旧的性。哈根认为,这种化了的性就不是本性,原因在于可化的性不可能是本性。显然,哈根对此的理解与其独特的思路有关,但这其中至少还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因为按照荀子“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正名》)来理解“化”,这种“化”固然没有改变性之为性的实质(“实无别”),但它可以转化或改变性的作用方式、性的表现形态。更重要的是,这与荀子对性的不同定义相关。《正名》篇对性有两种定义:一是“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一是“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而后一种定义的性,荀子显然认为是可化的,如荀子云:“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性恶》)“饥而欲食”是人的性情欲望的自然反应,欲食而不得则必有争;但今人饥而“不敢”先食而有所让,此中由“争”到“让”的转变,至少蕴含了这样一种解释:人的行动的动机已不是出于欲望,而是出于人对孝道的道德法则的敬畏,表现为心对评价性规范的“所可”。这种行动选择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以欲望为动机的动机机制,故荀子云,此“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从成就礼义之化的角度上说,我们不能说这种动机机制是“辅助性”的,而有其独立的意义;且在这种“化性”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很难理解有所谓的原初(自私)欲望的保留。
同样的,哈根在引用了荀子《儒效》篇“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后认为,荀子的这种说法表明这里所说的“化”并不是对性的转化,因为对性的转化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since that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do anything about)。无疑,哈根的这种理解也可以有不同解释,虽然荀子是以“性也者……”提出问题,但前面我们说过,荀子对“性”有两种定义,学者或称之为“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或称之为“及物”的性与“不及物”的性。而对此两种不同定义的性,在解释上当有所不同。固然,依哈根的意思,所谓不能化的性,指的是作为基本欲望的性,然而,基本欲望的性既然是人生而有的、无内容的能力,那么,从概念的严格规定上说,这种性在道德上理应是中性的,因而也不存在化不化的问题,哈根于此则不免同义重复;若进一步考虑到荀子“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的说法,那么,笼统地认为我们不能对性有所作为,显然并不十分严格,至少荀子明确认为:“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性恶》)荀子此处提出的“让乎国人”无论如何都应是“化性”后的一种表现,问题只在于如何理解这个“性”。
正因为如此,此处或许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把性区分为“吾所不能为”的性与“可化”的性?而这两种性有着不同定义,前者不能化而后者可化。显然,“让乎国人”的性是一种转化了的“性”,这种“性”在实质上与荀子把性定义为好利恶害的情欲是有所不同的。邓小虎认为:“或许我们可以诉诸另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不能为’的‘性’和‘可化’的‘性’并非同一种‘性’。‘不能为’的‘性’的确是‘不可学、不可事’的,但这仅指第一个定义下的‘性’,即人天生的质具。‘可化’的‘性’指的是第二个定义下的‘情’和‘欲’,虽然‘情’、‘欲’‘不待事而后生’,但却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加以转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化性”是“性”转化成了“伪”,而化性之后,性不复存在,仅有人为的动机(artificial motivations)保留,在这种情况下,性所代表的原初欲望也就不见了。但在Hagen看来,在《荀子》的文本中,有证据表明,“性”(作为原初欲望,又称为“原初自私欲望”)在修身之前和修身之后依然存在,如荀子云:“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又云:“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大略》)等等。他认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欲利而好义作为原初欲望是君子和小人之所同,并不会因为修身转化为君子后就改变了这种好恶。
然而,哈根此处所说的作为原初欲望的性只能是没有具体欲望对象的人的天生的能力(“生之所以然”),但他却把这种意义上的性理解为“原初自私的欲望”(original selfish desire)。首先,“原初自私的欲望”中的“自私”是一个评价性概念,而这种评价性概念只有当原初欲望能力表现为具体欲望以后才能成立,一种光秃秃的人天生的能力无所谓“自私”。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哈根对“求之之道”的“求”似乎坐定为“欲”之“求”,而无视了其还可能是“心”之“求”的解释,以致使他得出修身之前和修身之后原初自私欲望依然存在的结论。但是,若“求之之道”的“求”的主体不是“欲”而是“心”,那么,结论可能是“心”通过对道德原则的认知、所可(信念)发为行动,进而分别君子小人。如是,则行动的动机是出于“认知—信念”而非出于行动者的情性欲望。此外,哈根将《大略》篇所说的“好义”理解成与“欲利”一样的原初欲望,这种理解显然与荀子“人之性恶”的主张不相应,对此何艾克(Eric Hutton)从文本脉络的角度已有深入辨析,此不赘言。依哈根所论,荀子在《礼论》篇还认为“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这一说法意味着对于道德转化而言,不是“性”化为“伪”,而是“性”与“伪”的结合构成了“化”。
接着,哈根详细地分析了《儒效》《性恶》等篇中出现的三次有关“化性”的不同说法,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化性”本身并没有引起性自身的改变。而这里的性主要指的是基本欲望本身,换言之,“化性”所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具体欲望。故而哈根认为:“当我们引导我们的欲望时,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具体欲望,但却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欲望,或更准确地说,我们能改变我们的欲望所注意的具体对象。由于经验、知识和训练的原因,我们发现,欲望的某一具体对象,要么在考虑全局后并非是真正的最值得欲求的,要么与我们‘积累’起来的新的动机结构形成冲突。”为此,哈根引荀子《正名》篇所谓“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荀子思想的相关性。盖依哈根的理解,荀子此处所说的“节”明显不意味着减少(lessen)我们的欲望,它只是意味着要求修改(modify)我们欲望的作用形态或改变我们欲求的方式,这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欲望,比如“控制它们”。哈根把“节欲”的“节”理解成“修改”而反对把它理解成“减少”,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站在他个人立场所作的“强判断”;而修改的主体则诉诸于心或心之所可,故他引用史大海(Aaron Stalnaker)的话:“(心)能审核和计划,能考虑可能的行动和后果,能将不同的感知和想法关联到复杂的整体中,甚至能学会通过同意特定的目的或目标来否决对欲望满足的自发追求。”
二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按照荀子的说法,“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为何我们不可随顺当下的欲望,反而要“节制”我们的欲求?依照黄百锐的解释,原因是出于对长远欲望的实现的审慎考虑限制了我们对当下欲望的满足。如甲为了考上音乐学院实现当音乐家的梦想,他需要有足够的学费,为此他决定减少自己当下想吃“好吃但昂贵”的食物的欲望,以便为自己未来当上音乐家的梦想(欲望)积累基本条件。而荀子特别注意“长虑顾后”,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审慎的思维,故云:“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荣辱》)所谓“长虑顾后”,简单地说,就是当我们的心之思虑做出决断和行动时,不能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的欲望,而应该有深谋远虑的筹划和打算,亦即为顾及未来的长远目标而对眼前的欲望有所克制。对此,哈根认为,至少在早期阶段,儒家自我修养征途中的动机明显地来自于审慎的计算,因而荀子似乎最终是在一种基于欲望的后果主义和审慎的范式中来思考的,“而心之所可的基础是对规则和习性(regularities and propensities)的更为老练的理解,这些规则和习性揭示了实现个人满足的更有效的途径,亦即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当然,荀子并不提倡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都基于功利的计算,而是认为具有深谋远虑的审慎为自我修养提供了最初的动机。但在发展出德性之后,我们可以培养出一种基于非审慎的品质,不必每个决定皆出于功利的计算,而可以出于礼义或公义等更高的标准,只不过鼓励我们走上修养之途的依然是审慎的动机而非别的东西,如是我们乃可理解荀子所谓“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荣辱》)所蕴含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哈根认为,荀子对问题的思考似乎最终是在一个以欲望为基础的后果主义的审慎范式之中,人们之所以有酒有肉而不敢肆意,正是出于审慎克制的原则,“尽管没有绝对的保证,但儒家的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与审慎克制的原则相联系,人们的行为选择必须出于理智的权衡,见其“可欲”则必前后虑其“可恶”;见其“可利”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从而避免偏伤之患。而这里的“可”,依哈根的理解,其实义在最初当是某种“欲恶取舍之权”,亦即以理智的兼权熟计所表现出来的审慎和权衡,如荀子在《不苟》篇中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哈根对此解释道:“至少在最初,‘可’并不是建立在某种独立于欲望的道德感之上的,一开始只是欲望被审慎所折中……而一旦取得了进步,‘可’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审慎的计算,因为它会受到新的倾向(new dispositions)的影响(尽管旧的欲望仍然存在)。”正如我们看到的,此时我们可称之为“道德动机”最后战胜了个人的欲望。此处所谓的“道德动机”中的“道德”,其实质含义是“准道德”的意义,因为在荀子那里,这种“道德”不是先天意义上的,而是后天获得性的。故而哈根认为,即便在这个阶段,“可”仍然受审慎计算的影响,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算计”了,因为现在人们希望成为一个好人,变得好礼义了。此时人们形成了一种公共精神的情感,并开始珍惜高标准的生活。“想成为好人”“好礼义”便是获得性的新的动机结构。
此外,哈根对荀子的“养欲”和“好荣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荀子在《礼论》篇开头即点出了“养欲”的问题,“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紧接着说:“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但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荀子所说的“养欲”?养欲仅仅只是以物质的方式来达到对欲望的满足吗?在“欲多而物寡”的理论预设下,欲望又如何能够得到满足?盖依荀子对欲望的理解,人生而有欲,欲又具有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的特点,而欲望的对象又有限,如是,所谓“养欲”一词最直接的含义似乎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或“相对地”对欲望加以满足。这一说法意味着“去欲”“无欲”固然与欲望的本质特性不相容;同时,所谓欲望的满足也一定是在“求可节”(《正名》)的意义上的满足。
上述理解大体上是依荀子思想的脉络而来的,亦即在“欲不必穷于物,物不必屈于欲”的脉络中来解释“养”,这种意义上的“养”似乎主要着眼于经济的功能。另外,“养”也表现为“分”的结果,故荀子会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礼论》)。但荀子接着又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并进而认为:“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很显然,荀子在这里提出了“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等礼之“养”。而所谓礼之“养”的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规范的区分来限制和调节人们的欲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锦章指出,荀子所谓“礼者养也,具有经由教化使自己变得优雅的意义”。而Hagen接此话题进一步解释说,此处所谓的“优雅”(refinement)与其说是对旧品味的修正和转化,不如说包含了新品味的积累。换言之,养欲包含的教化及其所具有的优雅的效果,实际上是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动机倾向(new motivational disposition),故云“养欲可以发展出后天品味的效果,也就是说发展出新的动机倾向”。
一开始,人们可能不会发现遵循礼义的想法对人的行动具有内在的激发作用(intrinsically motivating),因此,人们可能需要外部刺激来尝试;然而,一旦人们因审慎的缘故尝试过它并发现它令人满意(被它“培养”)之后,一个人便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动机结构,并“喜爱”上它。因此,“当一个人养之于礼,发现它令人满意并逐步好其‘别’,那么,他就会有内在的动力进一步追求它”。此亦正如荀子所言:“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荣辱》)到那时,人们便有了内在的动机去践行礼义。如是,道德修养与转化的过程亦可说是一个“养欲”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就是使欲与礼义之道合而为一。
此外,涉及到好荣恶辱的问题,哈根认为,在荀子那里,我们的“可憎的”(detestable)情感欲望包含对荣誉的欲求,但欲求荣誉需要有智慧的引导;如果欲求荣誉的自然欲望没有与智慧相结合,只会产生不幸的后果。依哈根所论,小人和君子都珍爱荣誉,但君子通过正直的行为获得荣誉,因而君子会产生一种新的动机:他们想要真正的荣誉,而这总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实现的。哈根认为,事实上,每个人都欲求被尊敬,但有教养的人珍视被尊敬。他们原初的基于欲望驱动的计算引导他们追求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进一步发展出高贵的品性或德性。因此,人们一旦开始了这种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这种发展进程的动机效力就会是复合的而非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发展出来的对荣誉的喜爱超过了对荣誉的欲求,故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仅会认可、遵循真正的荣誉,而且他们也会在动机上倾向于这样做。
三
哈根的文章带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他对荀子欲望的分析,还是对荀子化性、养欲、好荣誉的解释,皆有其独特的看法。就文章的主要思路或框架而言,此文可以看作是远承倪德卫,近接万百安、黄百锐和克莱恩的相关讨论发展而来,所以阅读此文既有新鲜感,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似曾相识的味道。不难看到,哈根对荀子审慎之道的了解,尤其是他对荀子欲望理论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有文本解释的根据的。例如哈根把荀子的欲望区分为“基本欲望”与“具体欲望”,前者在荀子那里大体可以表示为人“生而有”的好利恶害的欲望能力,这种欲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去的”(《正名》),故称之为“基本欲望”;后者即人天生的这种欲望能力外接于物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反应,可称之为“具体欲望”。基本欲望不可变、不会变,因为这是人天生而有的;具体欲望可以改变,亦即借由教化、训练等改变其表现的方式,故习之于礼仪文理即可合于道。不过,有学者也指出,哈根对基本(原初)欲望与具体欲望的区分,尤其是他把基本欲望看作是自私、狭隘(selfish、petty)的,并为圣人和小人共有的论断,不仅无法解释“自私”判断从何而来(因为基本欲望只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的欲望能力),而且也与荀子对圣人状态的描述不相合。
然而,假如我们问,哈根何以对荀子欲望概念的分析会采取这种思路?这可能与休谟的相关论说对哈根的影响有关。休谟也将欲望区分为“原初欲望”(original desire)和“衍生欲望”(derived desire)或“被激发的欲望”(motivated desire),Hagen则把“原初欲望”既称作“基本欲望”,也称作“原初自私欲望”或“基本自然欲望”,把“衍生欲望或被激发的欲望”改换成“具体欲望”(desire for a specific thing)。在休谟那里,人的行动的动机必定是源自行为主体的原初欲望,而且这种原初欲望并不接受理性的管束,理性只能把衍生的欲望或被激发的欲望作为自己的评价对象;而哈根也认为,在荀子那里,化性之前和化性之后,原初欲望都不会改变,我们只是通过知识、经验以及训练等改变具体的欲望以形成新的动机结构。根据休谟对激情欲望和理性关系的理解,激发一个人行动的动机或动力只能来自于激情和欲望,而“理性对于我们的情感和行为没有影响”,或者说理性只是充当实现我们欲望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对此我们可以表达为,假如我们欲求φ,而通过Ψ能够实现φ,那么我们就有动机去做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休谟认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原初欲望总是在理性标准的管辖范围之外,不受理性的管束,不构成理性评价的对象,但衍生的(derived)或被激发的欲望(motivated desire)却可以构成理性的评价对象。如:“人生而有欲”是原初的欲望;而“我想吃上海的阳春面”或“我想吃四川的担担面”则是衍生的欲望,用哈根的话来说,即可以是具体的欲望,它意味着存在不同种类的食物,而理性在此发挥了选择的功能。盖理性的作用在认知,当理性的认知所提供的判断能够有效地为行动者实现其最强烈的欲望时,那么这种行动就是合理的。
然而,一个人行动的合理与否涉及评价行动的理由,这样的理由是独立于欲望之外而具有规范性的,是客观而普遍的,它不能由个人主观的欲望喜好来决定。休谟虽然注意到理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明显是在工具意义上说的。换言之,理性只是在原初欲望的主导下才表现出其设立标准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休谟会认为,行动的动机(欲望)即是行动的理由,理由的规范性不能独立于行动者内在的动机欲望。显然,休谟所谓的行动的理由(欲望),只是说明了理由的实践性,但却无法提供理由的规范性,若以此模式来解释荀子的动机理论,我们将会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难免会把荀子的道德理论推向非认知主义。
尽管哈根在文章中对休谟的理论未多置一词,但根据他对黄百锐的评论,我们却不难窥见一些端倪,盖黄百锐对荀子动机理论的解释在方法上基本上是休谟式的。而对此哈根则认为:“黄百锐的论点虽有其局限性,但我依然赞同一个非常相似的结论,此即基于相同欲望的内部动机,心之所可与不可能够克服当下的欲望……此外,这些动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而形成的,这种努力在更一般的欲望中具有推动作用。”所谓“基于相同欲望的内部动机”,就是基于欲望的长远满足的审慎动机。盖依黄百锐对休谟的理解,为了更好地实现长远的总体欲望,理性能够驾驭激情并克服当下的欲望,然而理性始终是作为工具服务于欲望的;而所谓“有意识的努力”所形成的动机,就是哈根所说的辅助性动机。
哈根对荀子的欲望概念和动机转化的观点并非全是休谟理论的翻版应用,他提出的经由教化训练发展出来的“辅助性”动机结构足以“克服”人的原初欲望并让人逐渐喜爱道德的主张,可以说是沿着学者相关研究而来的一个新发展。但哈根所谓新的辅助性动机足以“克服”(overruling)人的原初欲望的说法却不免含混,而他之所以称此为“辅助性”的动机是由于这种动机依然不能脱离原初(自私)欲望,不是一种独立的动机机制。对此,我们认为,相对于荀子的思想而言,哈根所说的动机转化只是某种“未完成的方案”,因为新发展的辅助性动机虽然可以“克服”人的原初欲望,但这种原初欲望却依然保存,且本质上是自私的。倘若如此,此一说法如何与“喜爱道德”的主张相融贯?对此或可辩解说,这恰与哈根所说的荀子是“以欲望为基础的后果主义的审慎范式”的说法相一致,然而,若这种新发展出来的“辅助性”动机仍然是以“自然欲望”为基础,则此一主张又如何与荀子所说的“全而粹”的君子能“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劝学》)的义理相协调?
哈根用休谟式的以欲望来解释行动动机,无疑是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主张,但很明显,若强执这一主张来解释荀子的动机理论却可能忽视荀子对“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解蔽》)、“求者从所可”“心之所可”(《正名》)等重要论述所可能包含的不同于欲望论的另一种动机论的解释面向。事实上,当哈根意识到万百安、克莱恩以及史大海重视荀子“心之所可”的主张时,一种基于“认知—信念”的动机解释模式已经呼之欲出,而不必取合于休谟的动机理论。从当代道德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学者对休谟式的欲望动机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就更明确地认为,“伦理学在人类动机中的基础并不是欲望”。有些人认为,道德信念本身便足以直接产生动机,例如单纯“相信履行承诺是正确的”,就会驱使相信此一命题的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道德信念本身会产生某种派生性的欲望,与评价性信念一起足以激发人的行动。
我们认为,以休谟式的欲望论来解释荀子的动机论,与荀子思想总体之注重“认知—信念”的动机模式、与荀子“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解蔽》)的主张在理论上似乎存在难以协调的张力。很明显,荀子思想非常注重理性的认知,此处所说的“可道”则有理由被理解为一种以“知道”为前提、但又不同于“知道”的一种信念的存在形式,即包含对伦理命题之真(“道”及其规范性)的心肯意肯的信念,如是,“可道”作为一种信念已表明可道者具有的激发性的心灵状态,而这种心灵状态足以产生动力以推动人们践行“道”。在这个意义上,荀子的“可道”之说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休谟式的欲望理论的独立的动机主张,亦即当一个理性的行动者A经由认知“真诚地”相信道德命题P而去做某事φ时,意味着该行动者A具有去做某事φ的动机。此时,对于欲求道德的人来说,“心”对“道”的肯可,一方面使得“道”成为人们“行动的理由”,另一方面,“可道”作为信念所包含的规范性和评价性本身又为人们提供了激发行动的动力。此正如荀子在《劝学》篇所说的,一个人极其热爱“道”时,就好像“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一样纯任自然,毫无勉强;撇开荀子对圣人境界的描述不论,即便一般的君子修养到达全而粹的境界时,感官所触,心官所虑,耳、目、口、心无非是“道”(参见《劝学》)。很显然,在这样一种动机转化中,我们似乎并不能看到哈根所说的“原初自私欲望”仍然存留,而激发人们闻道、行道的动力也并不来自“原初自私欲望”,而是来自“道”。尽管在荀子那里“道”的形成最初是出于人们审慎的考虑,但从荀子对“先王之道”的论述中不难看到,“道”既然是“古今之正权”(《正名》),表达了伦理命题之真,则人们对“道”的肯可便具有独立激发人的行动的动力。
(作者:东方朔,本名林宏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先秦儒学。)
【编辑:张晓芮】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