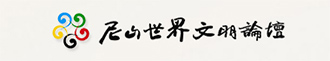探寻苏轼的“识画眼”——对话《东坡之眼》作者金哲为
2025-12-11 09:01:31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蔡可心 李斯羽

如何观看一位如苏轼般的文化巨人?当后世的目光多聚焦其文学成就与人生沉浮,《东坡之眼》一书却独辟蹊径,引导我们透过一方别样的棱镜——艺术之眼,重新凝视这位北宋全才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宇宙。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该书作者金哲为。透过这双“东坡之眼”,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绘画黄金时代的生成,或许还有一份如何在变幻世界中自处与奋发的古老智慧。
何谓“东坡之眼”
记者:“眼”常被视为神魂所注。与其他文人相比,苏轼这双“眼”有没有什么独特性?
金哲为:书名《东坡之眼》中的“眼”,取自苏轼“次韵李端叔谢送牛戬《鸳鸯竹石图》”中的诗句“知君论将口,似予识画眼”。苏轼在此向同僚李之仪提及的,正是自己鉴赏绘画的“眼力”。本书正是从艺术与绘画的视角进入苏轼的世界,此书名恰切点题。
观察苏轼的一生,恰如在他眼睛的“一睁一闭”之间。从少年到晚年,他始终在“看画”,而每个阶段所见,都对应着他当时的处境、思想与情感。他将自己的目光如此聚焦、如此持久地投注绘画世界,这是其独特之处。通过他的“眼”,我们也能窥见他生命的历程。
北宋是中国绘画的巅峰时期。我曾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借他的“眼”去见证那个巅峰时代的形成。苏轼无疑是最佳人选。
记者:选择从艺术史角度勾勒苏轼的一生,而非传统的文学或生平传记,是否有一种重新“观看”与“定义”苏轼的意图?
金哲为:无论是学习历史还是了解文学艺术,苏轼都是无法绕开的人物。后来,当我研究沈周乃至元明清的文人画家时,发现他们最终都需回溯到苏轼。很多原始的绘画理论,正是由他提出,后世脉络常要以他为源头。
通读苏轼的诗文集,我发现其中存在大量与绘画相关的内容。有的比较隐晦,有的则很直接,比如他的题画诗。还有许多地方,他运用典故已十分娴熟,读者若不留意,可能不会意识到其实是在谈画。
如今我们常把苏轼推上神坛,视其为伟大的文化符号,却较少关注他是如何“炼成”的。他绝非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了大量观画、交流、受指点、吸收灵感的过程,其各方面创作与思想融合,才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形象。
很难说是要“定义”苏轼,我更愿将这次写作视为一次“重新观看”,试图揭示以往未被充分注意的苏轼的面目,并探寻这些面目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枯木竹石”中的道与艺
记者:苏轼半生困顿漂泊,与其“不合时宜”的艺术表达有关系吗?您如何理解这种“人生厄运”与“艺术幸运”之间的关系?
金哲为:我所说的“不合时宜”,是指苏轼笔下推崇的“枯木竹石”。他曾将这三者并称为“三益友”。竹是“寒而秀”,在冬天百木凋零时仍保持风骨;木要“瘠而寿”,唯有枯瘦、不为世所用,才能得享长寿;石则须“丑而文”,以崎岖不平为美,光滑圆润反而失去意趣。单独看,这三者在其各自范畴中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存在,但苏轼却将它们组合入画,视作彼此知音。
苏轼十分认同老师欧阳修“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即文人往往因处境困顿而创作愈精。他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若论实际政绩,苏轼在杭州、密州、颍州等地任职时更有作为,而黄州、惠州、儋州皆为其贬谪之地,难有施展空间。他却视这三处为平生功业所系:一是贬谪状态使他得以远离政务,完成心中最重要的著述,如《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均在海南最终修订成稿;二是这三段经历塑造了后世所知的苏轼——如今许多人未必清楚他曾任颍州、扬州,却几乎无人不知黄州、惠州与儋州。
历经仕途坎坷,苏轼更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思想。绘画成为他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表达思想时的替代空间。尤其在宋代王安石新儒学占据主流的思想环境下,艺术反而为他开辟了一片可耕耘的天地。
这也回应了我为何写这本书。最初或许只为探讨绘画,但深入其中便发现,苏轼论画的标准、评人的尺度,从来不止于艺术。其背后与他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文化立场贯通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他人生的“厄运”恰恰成就了其艺术的“幸运”,也让后人得以通过画眼,窥见他更完整的精神世界。
记者:在诗画、书信的只言片语间解读其画论体系与艺术精神,如同在碎片上架设桥梁。您认为其中的难点是什么?
金哲为:首要的困难在于寻找与汇集。苏轼关于绘画、收藏的见解,大多散见于给朋友的书信、诗歌或某篇杂记中,且往往并非专为论画而作,因此材料非常零散。不仅如此,还需要尽力还原他可能见过的“画”。有些经历他未必写入文字,这就需要考证他去过的地方、交往的朋友及其收藏,尝试构建一个属于苏轼的“视觉经验库”。此外,由于他常娴熟化用典故,许多表面上与绘画无关的文字,实则暗藏画论,解读起来颇为晦涩,需要仔细辨析。
第二个难点,在于找到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理解苏轼的艺术精神,必须追溯其源头,即塑造他世界观与行为准则的儒家经典,尤其是《易经》。我自己也因为研究苏轼而去研读《易经》,发现他应对人生顺逆的许多选择,几乎完美契合了《周易》所倡导的君子处世之道。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典范。
因此,我的工作有点像从一片叶子追溯到枝干,再回到滋养它的土地,但最终仍需回到那片叶子本身,完成闭环。
在“知时”与“天命”间
记者:为写作此书,您从2021年底就展开了有计划的阅读。长年沉浸在苏轼的世界,是否有过某个与其“灵魂共振”的时刻?
金哲为:这样的时刻非常多。苏轼就是这样,了解得越深、阅历越丰富,重读时的感悟就越是不同。我认为他骨子里是极为入世、积极践行儒家精神的君子。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总能豁达面对,保持内在的坚定。
以前我对苏轼的印象比较模糊,常将他的成就归因于天赋或性格。但深入研读后,我发现他始终恪守着一些根本准则:比如做人上的“直道”,他并非不明世事的“不合时宜”,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知时”的人。所谓“知时”,在于他能在不同境遇下作出恰当的应对,并安然处之。这并非随波逐流,而是深刻洞察现实后的主动选择和持守。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心中苏轼形象逐渐清晰、简化的过程——穿过他多样的面目,抓住那根“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无论外界如何变迁,他的生命始终围绕这个核心展开。
记者:透过一幅幅画作和背后的文人交往趣事,您看到的宋人精神世界,整体上具有怎样的气质与内核?
金哲为:最突出的一点,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乐天派”。无论遭遇何种困境,他们似乎总能以乐观、通透的态度去面对。较之唐代文人常有的深沉悲慨,宋人更显出一种理性而达观的调适能力。
此外,宋人非常善于从与自然的相处中获得启示与精神滋养。无论是苏轼、文同从墨竹、枯木、怪石中体悟生命态度,还是王诜、宋迪通过寄情山水来治愈心灵,抑或李公麟借画马寄托对人世的理解,他们都在自然世界中寻找灵感,并通过观察与描绘,试图理解万物运作之“理”。这又与《周易》的智慧相通——世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君子贵在知时处变。
宋人,尤其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其实非常相信“天命”。这种“天命观”并非消极的认命,而是一种深刻且积极的信念。这种观念或许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写道:“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他认为上天赋予自己特定的境遇与禀赋,绝非偶然,其中必定蕴含某种用意与使命,即“天将降大任”的意味。这并非被动承受命运,而更近于孟子那种“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的主动承担精神。苏轼深受此影响。他在总结自身遭遇,如乌台诗案后的贬谪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困境多是“人恶”,并非“天穷”。他相信造化的安排皆有深意,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其必然的目的。基于这种信念,人自然不应怨天尤人,而应思考如何积极回应当下的处境。
这种微妙的“信命”与“尽性”相结合的状态,在苏轼对《柏石图》的咏叹中体现得尤为典型。这幅画描绘了一株柏树生长于两石之间的狭缝中。苏轼提到,韩愈认为柏树既然被巨石所困,难以长大,不如移栽平地,即便伤根,终有长成千尺高树之日。但苏轼认为,此画的立意恰恰在于“嘲讽”韩愈的这种想法。“天命本如此,岂有可移理。”如果柏树的天命就是生于石间,那么“与石相终死”便是它应有的生命轨迹,何必非要移栽?苏轼所信奉的“天命”,是一种让人在认清必然性的同时,依然能焕发最大主体性与积极性的精神资源。它不是“老天为何如此对我”的愤懑,也不是“我就这样了”的放弃,而是“既然老天如此安排,那我便在此境遇中,活出最饱满、最富意义的状态”。这种在接纳中进取、在限制中舒展的智慧,正是其精神世界中极为深刻而独特的一面。
【编辑:董丽娜】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