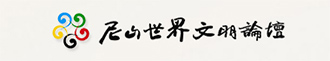黄玉顺:论经典诠释中的主体转换——《中庸》学史的启示
2026-02-12 10:15:32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黄玉顺
经典诠释的“主体转换”是经典诠释学的一个根本方法论问题,却尚未引起重视,更未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专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庸》学史,阐明“经典诠释的主体转换”问题。作为儒家核心经典“四书”之一,《中庸》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反复深入研究。张兴的专著《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书名提示了两个要点:其研究对象是“《中庸》学史”即《中庸》诠释史,其研究角度是“经学视野”。而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庸》学史的研究来说,书稿最重要的推进是触及了“《中庸》诠释的主体转换”这个根本问题,散见于全书之中,而集中总结于“结语”之中的“《中庸》行为主体的演变”,其意义不限于《中庸》研究,还关乎一般经典诠释学中的普遍方法论问题。
一、经典诠释的主体问题
谈到“《中庸》学史”,必然涉及“主体转换”问题,因为“历史”总是某种人即某种主体的历史;谈到“经学视野”,同样涉及“主体转换”问题,因为“经学”本身就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即同样是某种主体的历史。
(一)经典诠释的“主体”问题
为此,首先必须澄清“主体”的概念。“主体”所指的当然是人,即某种主动者和能动者;但是,这个词语的使用极为广泛,歧义丛生。例如中国哲学界,有学者说:《中庸》“已经摆脱了先秦以来天命思想的束缚,将其和人性放在一起”;“在此,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萌发”。这里的“人”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其“主体”概念乃是一般人本主义哲学的观念。又如翻译学界,讨论了《中庸》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而本文所说的“主体”,特指经典文本及其诠释所涉及的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
一是“行为主体”,这是《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经典本身及其诠释所诉诸的对象,他们是“应当具有某种德行”的行为主体。朱熹引游氏说:“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具体到《中庸》这个经典文本,行为主体即某种应当具有“中庸”这种德行的主体。如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人们已经长久地缺乏中庸的德行了。书稿“结语”部分所谈的《中庸》行为主体的演变,就是从“明君重贤用贤”(君臣)到“学者修养工夫”及“诚之者修道”(贤人)、再到“孔子立教改制”的主体德行转换。
二是“诠释主体”,指经典的作者与历代诠释者。具体到《中庸》这个文本,诠释主体指《中庸》的作者与历代诠释者。书稿“结语”所谈的行为主体的演变,实际上取决于这种诠释主体的转换:“明君重贤用贤”(君臣)的诠释者是帝制时代前期的汉唐儒者(郑玄、孔颖达等);“学者修养工夫”及“诚之者修道”(贤人)的诠释者是帝制时代后期的宋明儒者(朱熹、王阳明等);“孔子立教改制”的诠释者则是近代儒者(康有为)。
(二)经典诠释主体的“转换”问题
上述主体“演变”,就是经典诠释的“主体转换”。这是因为:经典诠释史的根本问题,是理解经典的作者及其历代诠释者的“时代”转换;而经典的作者及其诠释者,都是历史的某种“主体”;因此,经典诠释史的根本问题就是“主体转换”。
1.历史时代的划分。书稿对《中庸》学史的梳理,划分为五个时期,即汉魏、隋唐、两宋、元明和清代。这种划分当然是有道理的,符合中国学术的历史形态的传统划分方式。不过,它们均属广义“经学”时代。在笔者看来,为了在更宏阔的背景上讨论“经典诠释的主体转换”问题,我们也可以超越“经学”视域,拓展到前经学时代(轴心时代)和后经学时代(现代),从而做出更具历史哲学意义的划分:
| 领域时代 | 历史 | 生活方式 | 社会形态 | 学术形态 | 《中庸》学史 |
| 前轴心期 | 商周时代 | 宗族生活 | 王权封建 | 学在王官 | |
| 轴心时代 | 春秋战国 | 第一次转型 | 体制转型 | 百家争鸣 | 《中庸》成文 |
| 后轴心期 | 自秦至清 | 家族生活 | 皇权郡县 | 汉唐经学 | 汉唐《中庸》学 |
| 宋明理学 | 宋明《中庸》学 | ||||
| 新轴心期 | 近代 | 第二次转型 | 体制转型 | 近代新学 | 近代《中庸》学 |
| 现代 | 现代 | 个体生活 | 现代体制 | 现代学术 | 现代《中庸》学 |
所谓“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都发生在广义“经学”时代:汉唐《中庸》学发生在帝制时代前期,宋明《中庸》学发生在帝制时代后期;至于近代《中庸》学,其“经学”指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帝制时代的“经学”,而是某种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新经学”。
因此,《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强调的“经学视野”,涉及这种历史哲学的背景。大致来说,商周以降的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时代,即王权时代(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帝制时代)和民权时代;中间存在着两次社会转型时期,即先秦的轴心期(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时期。本来意义的“经学”,作为帝制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以“唐宋变革”为界线,它可以分为帝制时代前期的狭义“经学”和帝制时代后期的广义“经学”。
2.两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上述“行为主体”和“诠释主体”这两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并非行为主体决定了诠释主体,而是诠释主体的转换决定了行为主体的转换:有怎样的诠释主体,就会有怎样的行为主体。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同为《中庸》诠释,为什么行为主体会从轴心时代以及帝制时代前期的“明君贤臣”转变为帝制时代后期的“贤人”、又转变为近代意义的“教主孔子”?显然,这是诠释主体的转变导致了行为主体的转变。更具体地讲,汉唐时期的儒者诉诸明君贤臣;宋明时期的儒者不仅如此,而且诉诸包括儒者在内的社会精英;近代康有为则诉诸“孔教”的教主孔子的“改制”。
3.主体转换的生活渊源。如果行为主体的转换源自诠释主体的转换,那么,诠释主体为什么会发生转换?这是因为时代的转换——生活方式的转换导致的社会形态的转换。简言之,特定的主体及其主体性是由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给出的。这就令人想起孟子的著名论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里的“诗书”指经典文本,“其人”指诠释主体,“其世”指诠释主体的时代背景;而“注”这种活动则属于特定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孟子的意思是说:论其世才能知其人,知其人才能读其书。这种经典诠释观念,笔者称之为“注生我经”,意思是:并非经典决定了注释,而是注释活动决定了注释者乃至于经典。借用王船山的话语来讲,不仅作为诠释主体的注释者,而且经典本身,都在“日生日成”。
二、《中庸》文本的主体问题
按照孟子的诠释学思想“论世知人”,要理解《中庸》本身,首先需要理解《中庸》的作者;而要理解《中庸》的作者,又需要理解《中庸》作者的时代生活。
(一)《中庸》的时代
关于《中庸》文本产生的时代,传统说法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朱熹《中庸章句》所说:“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此前,程颐即已说过:“《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子思即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孔氏,名伋,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
对于程朱的上述说法,后世颇多异议。《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有专节“《中庸》成书时代考辨”,列举了五种说法,即战国早期说、孟子之前说、孟子之后说、汉初所作说、秦汉所作说,并认为“《中庸》应该出现在秦汉之前,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战国时期,最早可能成书于战国早期”。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关于《中庸》文本产生时代的五种说法,可以分为两类:战国早期、孟子之前、孟子之后,均属轴心时代,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时代、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时代;秦汉所作、汉初所作,均属帝制时代、思想领域正在走向“独尊儒术”实则“阳儒阴法”的时代。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可不辨;否则,恐怕无法理解《中庸》学史。
笔者倾向于《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的观点,即《中庸》产生的时代是在“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代传世的《礼记·中庸》就一定是最初的原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转型”,即所谓“周秦之变”,亦即从宗族生活方式下的王权封建社会转向家族生活方式下的皇权专制社会。所以,笔者说过,《中庸》“其实是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文本”。
上述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庸》涉及的两种主体的时代特征:
(二)《中庸》作者的主体性
关于《中庸》的作者,《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辟有专节“《中庸》作者考辨”,认为“学术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子思所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更稳妥的说法,可以说《中庸》并非子思个人的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子思及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的集体著作,这个集体就是所谓“思孟学派”。“思孟学派”这个概念,最初见于侯外庐初版于1944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该书第八章即题为“儒家思孟学派及其放大了的儒学”。通常认为,子思是曾子的弟子,这种看法最早出自孟子,即认为“曾子、子思同道”。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即司马迁所说的“受业子思之门人”。韩非谈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两者分属两派;最早将两者视为一派的是荀子,认为“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根据多数学者的意见,“思孟学派”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群体谱系:(孔子—曾子—)子思—佚名—孟子。
以上关于“思孟学派”的讨论,意在确定《中庸》作者群的群体主体性,即他们所具有的基本思想意识。这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中国轴心时代“周秦之变”这个时代背景。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就是所谓“礼坏乐崩”、重建秩序:从宗族生活方式转向家族生活方式,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从王权与诸侯大夫等贵族的分权转向皇权的乾纲独断,如此等等。
而当时的儒家,基本上属于“士”这个阶层,处于贵族与民众之间:一方面,他们作为“四民”之一,被列入“民”的范畴;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入仕为官,甚至还可能跻身贵族。《穀梁传》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关于其中的“士”,范甯注:“学习道艺者。”杨士勋疏:“何休云:‘德能居位曰士。’范云:‘学习道艺者,是以为之四民;若以居位,则不得为之民。’”(这里“为之”犹言“谓之”)这就表明,“士”区别于“农、工、商”,在于他们乃是知识精英,可以由“学习道艺”而“德能居位”。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当时及后来儒家的一种独特的价值立场,那是双重价值承诺,可称之为“平民精英主义”(civilian meritocracy):一方面站在民众的立场,要求“务民之义”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另一方面却又藐视民众的智能,认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们通过《中庸》这个文本,诉诸两类不同的行为主体,即“庶民”(平民)与“君子”(知识精英、政治精英)。
(三)《中庸》诉诸的行为主体性
通过上述《中庸》作者的主体性,我们才能理解《中庸》所诉诸之对象的主体性,即哪些人应当、是否、怎样才能具有“中庸”的德行。
首先,《中庸》通过先天人性论而认定:每一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天然地具有“中庸”的德性。所以《中庸》开宗明义地指出:“天命之谓性。”然而,在后天的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能保持这种“中庸”天性即“中”或“诚”的天性,而分为两种人:一种人“自诚明”,可以“率性”;另一种人则“自明诚”,必须通过“修道”之“教”使其恢复天性。这两种人的区分标准,并非社会地位,而是按天然情感“发”出来之后能否“中节”来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节”,意谓“合礼”,即毛亨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
然后,根据上文所说的“平民精英主义”立场,《中庸》将其诉诸的行为主体及其德行分为两类:
1.民众:“庶民”
从儒家平民主义立场出发,“中庸”的德行诉诸社会民众,即其所谓“庶民”。《中庸》提出了“庶民”的概念:“君子之道,本诸身,徴诸庶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子庶民则百姓劝”。对于庶民,《中庸》表达了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是“重民”,表现出对民众的尊重。《中庸》指出:“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徴,无徴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徴诸庶民……”郑玄注:“徵,犹明也”;“‘徵’或为‘证’。”孔颖达疏:“徵,验也”;“须有徵验于庶民也”。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取信于民、取证于民。这里透露出了对民众主体性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令人想起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对民众“逐利”德行的肯定。当然,这并不是现代“民权”观念,而是出自传统的“民本”思想,如《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然而另一方面却是“轻民”,表现出对民众的轻蔑。《中庸》指出:“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但是需要注意:这种“轻民”应当说是“轻人”,即并非专门针对民众,亦针对君子:“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甚至孔子说他自己:“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这是基于上文提到的儒家的一种基本设定:人皆具有先天的“中庸”德性,然而并非人皆具有后天的“中庸”德行;毋宁说都缺乏这种德行,所以实际上都需要“修道”而“自明诚”。
2.精英:“君子”
从儒家精英主义立场出发,“中庸”的德行诉诸社会精英,即其所谓“君子”。《中庸》所说的“君子”,包括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这些行为主体,涵盖了《中庸》提到的诸如天子、君臣、大臣、群臣、诸侯、大夫及士、圣人、圣者、大德者、贤者等。
针对这些行为主体,《中庸》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德行要求:
一方面是“修身”。《中庸》明确提出:“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社会精英的首要功课:“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修身则道立”。那么,什么是“道”?那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因此,“中庸”的德行本质上就是“诚”的德行,也就是“仁”的德行,所以《中庸》又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另一方就是“治民”。《中庸》提出:“君子以人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思孟学派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分工观念,如孟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民”,这与《大学》的“内外”思想结构一致,即由内向的“明德”而达至外向的“亲民”或“新民”。《中庸》进而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按照儒家精英主义的立场,“治人”的根本就是“化民”。《中庸》的诉求,就是曾子所说的怎样才能使得“民德归厚”,亦即“化民成俗”;“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中庸》甚至将“化民”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那么,怎样才能“化民”?《中庸》指出:“《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这就是说,赏罚威仪只是其“末”,其本仍在于“仁”或“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但是,与此同时,回到平民主义的立场,“治人”的目的乃是“宜民”。《中庸》指出:“子庶民则百姓劝……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进而引证《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并举圣人为例:“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将这种“宜民”之“诚”概括为“成物”:“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三、《中庸》诠释的主体转换
上节讨论的是《中庸》本身的主体问题,本节将讨论《中庸》主体的转换问题。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及其伴随的思想观念的“轴心时代”,《中庸》的诠释主体和行为主体都发生了时代转换。
(一)《中庸》诠释主体的转换
这里的主体转换,首先就是诠释主体的转换,即《中庸》诠释者的转换;更确切地说,是从《中庸》作者的视角转为《中庸》诠释者的视角,两种视角属于不同时代的社会主体。
1.“不召之臣”:《中庸》的作者群体
上文谈到,《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他们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知识精英。上文讲过,他们身处贵族与民众之间。按孟子的说法,他们乃是“不召之臣”: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
这里所说的“臣”,并不是君主的“臣下”之意,而是“臣民”之意,正如孟子所说:“在国(城市)曰市井之臣,在野(乡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孟子认为,臣民之中的有德之“士”“君子”,可以拒绝君主的召见、召唤。孟子以子思为这种“不召之臣”的范例: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这就是说,子思不仅并非君主之“臣”(臣属),甚至不是君主之“友”,而是君主之“师”。孟子指出:“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孟子进一步阐述了“士不托诸侯”的原则,意谓不委身于诸侯、不臣属于诸侯,以此强调“士”的独立性。万章问:“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答道:“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紧接着便以子思为例:“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
以上“士”即“不召之臣”的存在,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时代,王权衰落,诸侯并立。因此,士人不必委身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诸侯国家,而可以自由迁徙流动,“周游列国”,如孟子那样“传食于诸侯”。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2.“莫非王臣”:帝制时代的诠释主体
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已经从封建时代转入“大一统”的帝制时代,真正彻底地实现了《诗经》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的本意所指,并非人们通常的理解,孟子即已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在皇权“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真正独立的“士”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也很难存在。知识精英为了生存,就必须通过察举或科举而进入帝国体制,成为皇权的臣属。正如程颐所说:“夫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来处,乃得于君也。必思所报其君,凡勤勤尽忠者,为报君也。”
这里就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例,说明帝制时代的《中庸》诠释主体。这是因为:正是二程率先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形成帝制时代后期的儒家核心经典“四书”体系。程颢著有《中庸义》,程颐著有《中庸解》。
对于思孟时代的士人独立状态,二程不以为然:“孟子之时,大伦乱,若君听于臣,父听于子,动则弒君弒父,须著变,是不可一朝居也。”二程理学讲“理”,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程颐甚至认为:“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也。”在他看来:“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这就是说: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生活,都不过是公共生活的“寄寓”;而公共生活,则“不过君臣”而已。
因此,二程这样理解、实为误解孟子:“孟子之于齐,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尝不迟迟顾恋。……君臣犹父子,安得不怨?”程颐甚至这样通过韩愈理解君臣关系:“韩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得文王心出来,此文王至德处也。”至于《中庸》,程颐这样解释“诚者自成”:“如至诚事亲则成人子,至诚事君则成人臣。”这已经大异于士人孟子所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也大异于士人荀子所讲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当然,这种诠释主体也自有其时代背景的缘故。程颐就称:“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他以孟子的“执中无权”会导致“举一而废百”,来理解《中庸》的“时中”,由此强调时代背景,倒也不无根据。传统注疏对《中庸》“时中”的解释不确切,朱熹乃解释为“能随时以处中”,指出:“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但这种“随时”决不能是孟子所批判的那种“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乡原”。因此,程颐进而指出:“夫圣贤之处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则有时而独异,盖于秉彝则同矣,世俗之失则异也。不能大同者,乱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二)《中庸》行为主体的转换
不仅《中庸》的诠释主体,而且其所诉诸的行为主体,也随着时代的转换而发生了转换。表面来看,帝制时代的诠释者们依然是在谈论《中庸》所谈的行为主体“庶民”与“君子”(诸如天子、君臣、大臣、群臣、诸侯、大夫及士、圣人、圣者、大德者、贤者等),但实际上,这些称谓的概念内涵已经发生了时代内容的变易。
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有循于旧名”。不过,所谓“循于旧名”,在时代的转换中,这些“旧名”已被赋予“新实”,即已经变成了新的概念。这种转变何以发生?荀子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所谓“约定俗成”,这里意谓“旧名”赋予“新实”的本源乃是作为“流俗”的时代生活。
这里且以朱熹《中庸章句》为中心,来加以分析。例如《中庸》谈到: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这里的行为主体,固然是指的君主。但在诸子时代,君主不仅指天子,更是指众多的诸侯国君;而在帝制时代,君主就是皇帝。朱熹引吕氏说:“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然必亲师取友,然后修身之道进,故尊贤次之。道之所进,莫先其家,故亲亲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国,故子庶民、来百工次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远人、怀诸侯次之。”这里所解释的对象,其实已经不再是王权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例如:“百工”原是王宫之工,本无需“来”,现在需要“来”之;“诸侯”已经不复存在;“由其国以及天下”的“远人”,其实是帝国朝贡体系;如此等等。
最根本的是:所谓“王”或“天子”,在思孟时代和帝制时代,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孟子指出,“王”不过是一种“爵禄”而已:“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而在帝制时代,《中庸》诠释之中的所谓“王”或“天子”,所指的就是皇帝。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体系。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庸》本身作为“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文本”,其时代背景是从封建到专制的过渡,因此,其中已经有一些属于皇权专制“大一统”的议论。例如:“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朱熹集注:“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制为礼法,以及天下”。许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这并不是封建的“周制”,而是帝制的“秦制”。《中庸》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朱熹指出“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实际上就是作为唯一立法者的皇帝。所以,朱熹解释《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引吕氏说:“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过矣。”这里的“天子”,显然也是帝制时代的皇帝。
结语:《中庸》诠释的现代转化
以上讨论的主体转换,其时代背景是“周秦之变”,即从宗族王权的封建时代转变为家族皇权的帝制时代。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周制”转向“秦制”。那么,这种讨论对于今天的《中庸》研究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呢?这里首先还是时代背景问题: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即“古今之变”。显然,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庸》诠释,应当超越帝制时代的“经学视野”。
因此,面对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体制的现代化,要盘活古代经典,就必须自觉地进行诠释主体和行为主体的“现代转换”。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庸》本身就有一种经典诠释学思想;其中的“‘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帝制时代的知识精英重新诠释《中庸》,那是一种“温故而知新”;我们今天重新诠释《中庸》,也是一种“温故而知新”。这里的关键之一,即“主体性的更新”:首先是诠释主体的更新,《中庸》的诠释主体必须具备现代价值观念,否则“未能成己,焉能成人”;然后是行为主体的更新,今天的《中庸》诠释,其对“中庸”德行的诉求,不应当再诉诸“帝王将相”,而应当平等地推展到所有社会成员。
当然,这里同样涉及儒家的“平民精英主义”问题。就诠释主体来说,今天的《中庸》诠释者,尽管并非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但仍然具有士人的基本特征,即处在精英、庶民之间。就行为主体来说,对于今天的《中庸》诠释所诉诸的对象,儒家的平民主义应当体现为“人民主权”的观念,而其精英主义只能体现为“代议”的观念。同时,这两类行为主体,都应当具有“中庸”的德行;而与此同时,“中庸”德行的具体内涵也应当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兹不赘述。
总之,对于激活古典、应对时代问题来说,“经典诠释的主体转换”乃是一般经典诠释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也是儒家“自由保守主义”的必然选择。
OnThe Replacement of Subjec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An Inspir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StudyingThe Mean
Huang Yu-shun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ssue in classical hermeneuticsthat the "replacement ofsubject" in the interpretationof classics, encompassing the replacementof both the "interpretive subject" of classical texts and the "behavioral subject" it appeals to.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style and the resulting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ve subject and behavioral subject for the classicswill inevitably undergo corresponding replacement.Taking the history of studying the Meanas an example, its interpretive subjectswerethe authorsand interpreters of the Meanthroughout history, especially the Song and Ming Neo-Confucians in the late imperial era; The behavioral subjectswerethe objectsthose the cre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placedhope on, namely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gentlemen" (social elites).Facing themodern lifestyl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system brought about by them, in order to revitalize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including the Mea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ciously carry out a modern replacement of interpretive and behavioral subjects, endowing their "old names" with "new realities" that are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modernity.
Keywords: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Replacement of Subject;History of Studying The Mean
【编辑:董丽娜】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